
原標題:
前面説過,中國的文明態勢,是一種自新型、中和型的文明。
中國是自新型的文明,這緣于儒家經典中的論述。《大學》開篇就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親民”就是“新民”,是要使人自新的意思,成就一個新我,改過向新、除舊布新,這就是學習的目的。對人如此,對國家、對民族、對一種文明而言,更是如此。中華文明歷史雖久,卻不是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文化就提出了“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提出了“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國家雖古老,卻不忘自我更新、推陳出新,每一天都能如新生一般吐故納新。所以中國的文明,不是一成不變的,是在堅守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始終兼容並蓄、與時俱進著,這才成就了源遠流長的生命力,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鮮活至今的古文明的原因所在。
中國更是中和型的文明,“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對“和”的追求,在中國既是道德觀念、也是哲學理念,既是藝術準則、也是生存方式的要求。有些西方國家由海洋文明形成的海盜意識,構成了踏上新大陸後對當地的掠奪行徑、侵佔歷史,海盜式文明,以奪取他方資源為生存本能。而中國的農耕文明卻是以自給自足、自食其力為生存模式和思維方式,並且在土地上形成了團結緊密的家族意識,為了耕種,世世代代企求的都是穩定與和平,厭惡戰爭和變數。農耕民族的子孫都要按照祖輩經驗來種植和收穫,最怕由亂生變、影響收成。中國人這種熱土觀念,轉而昇華為一種廣泛的教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中國人堅信,財富生於自己的土壤,而非掠奪他人的土地。甚至,連財富也只是末節和結果,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而最為根本的道德,就是“致中和”。中道,就是不偏不倚、正中正好、符合常理、恰當其分的道路,用中是手段、和諧是目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各在其位、萬物健康生存——各在其位、健康生存,也就喻示著各安其土、彼此尊重,中正仁和、和平共處。
所以有些國家對中國“國強必霸”的判定、認為中國這頭雄獅萬萬不可醒來的擔憂,是站在西方行為立場上、順延西方固有意識形態的一種以己度人,而非身處中華文明歷史洪流中、作為承前啟後一脈傳承的一種思維方式。

西方文明的意識主導下,還産生過一種深入人心的論斷,就是亨廷頓先生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他認為,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來自文化差異,而且主要是在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三者之間構成“文明的衝突”。這種論調不無道理,加之九十年代以來局部戰爭的爆發、恐怖事件的上升,讓人們更加信奉“文明衝突論”。
然而,亨廷頓先生強調的是不同文明形態之間差異的部分、側重的是不同民族之間對立的情緒,卻忽略了各種文明之所以形成,正是出於人類共性上的那些價值追求和道德理念,比如對真善美的嚮往、對公平正義的肯定。在文明之間,必然是共性大於差異,共同的美好訴求,是各地區文明不約而同生成存在的基礎。文明,就是為區別野蠻而存在的。
何況,任何一種健康文明都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而是流動的、發展的。僅以靜止形態看文明,每種文明都是對立性的獨自存在;若以運動形態看文明,文明之間便是相互交融的、滲透的、影響的態勢,差異並不阻隔對話,異同也不阻礙交流。
而把世界的衝突歸納為“文明的衝突”,歸根到底,是因為始終抱著“衝突”的眼光在看世界,認為世界不是這樣衝突、就是那樣衝突,而這,恰恰是一種典型的妄圖主導他國、稱霸世界的西方文明的思維。而在中國的文明語境裏,傳達的卻是“天下大同”、“四海昇平”的理想,這也正是中國一直強調要“和平崛起”的思想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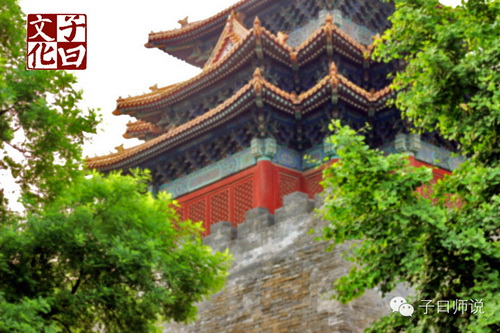
(三)現代化文明
當中國通過經濟、軍事的強大改觀了自己,又通過政治、文化的強大改善了自己,堅持著自我文明中貫穿始終的中國精神,有朝一日,將不難實現在現代化文明面前重新引領世界。而這種引領,不是靠武霸的力量,相反,是靠和平的力量。這就涉及到“文明”的狹義概念:一個國家,一個個人,怎樣才是文明的,尤其是,怎樣才是符合現代文明的。
清朝末年,屢戰屢敗,民族危亡,於是嚴復先生將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翻譯到中國,第一次為國人介紹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這個來自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強烈撼動了國人的神經,原來,落後就要挨打,弱小就被淘汰!
《天演論》的宣揚有其特殊時代背景,然而在今天,將“弱肉強食”的理論照搬到現代文明,是不對的;將自然規律完全視作人類社會法則,是錯誤的。不要忘記,達爾文生物進化學説的原點,是研究物種演化,而不是社會倫理。但人類文明,恰恰屬於社會學説,而不是生物學説;人區別於動物,就是因為人類文明超越了動物天性。如果人類社會要拋棄自身本來優越于動物界的文明意識,而退回到以野獸本性對待同胞,那麼才真是物種的退化!何況達爾文進化論本身是否成立,也早已經被質疑。
倘若“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理由在人類社會成立,那麼就會給偏激的種族主義者、極端的宗教分子以強大藉口,去肆無忌憚地屠殺他人。而人性的文明意義卻在於,能夠在堅持平等的大原則下去格外有意識地保護弱者,以維持社會的公正。可以説,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才反應出文明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