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視網|視頻|網站地圖 |
| 客服設為首頁 |
最高人民法院5月29日下發通知,公佈了2012年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涉及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的賠償標準,具體數額為每日162.65元。眾多網友認為,雖然金額上調但總體水平太低,無法彌補公民真正的損失。冤假錯案不只傷害了公民無價的自由,也一次又一次地動搖了法律的權威。自由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如何令受傷的人得到安慰,是國家賠償最應該思考的事情。 [詳細]
第28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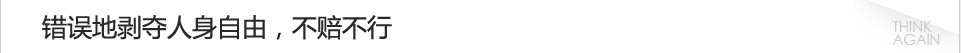
38年前,當時只有19歲的美國小夥子詹姆斯被指綁架並強姦了一名9歲男童被判終身監禁。2009年,通過DNA檢測確定,詹姆斯根本不是真兇,無罪釋放後,詹姆斯將獲得175萬美元的賠償金。
人身自由在案件審判中被錯誤地剝奪,被害人理應得到賠償。美國十五個州設有冤獄賠償法例,但標準卻不大相同,一名因強姦罪坐了十六年半冤枉監的男子,得到的賠款相當於每天4.6美元;2009年德克薩斯州將“冤獄”的一次性賠償額增加到冤枉服刑每年8萬美元,外加此後每年4至5萬美元的終身年金,是美國國家賠償最高一個州。
國家賠償款從哪來,美國的刑事案件由陪審團審判,嫌疑人是否有罪有群眾做出決定。因為陪審團由普通民眾擔任,如果沒有行政力量的粗暴介入,納稅人掏錢進行國家賠償,也是合理的。
有時,侵害人身自由的並非某個錯案,也不是司法過程不公,立法時由於考慮不週導致違憲也會侵害特定群體的自由。在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立法賠償是國家賠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996年,日本國會通過《廢止麻風預防法法案》,廢除了《麻風預防法》。後者曾規定了麻風病患者及其家屬需接受長期的強制隔離,這種痛苦在《麻風預防法》被廢除之後依然難以得到消除。原麻風病患者們根據日本《國家賠償法》,在多家法院提起以國家為被告的損害賠償請求訴訟。2001年,熊本地方法院的判決指出國家依據《麻風預防法》實施的隔離政策嚴重侵害了患者的人權,需進行立法賠償。“國家法律不能為了一部分公民的利益,而犧牲特定人或少數人的利益”,法院的判決理由如是説。
國家或法律錯誤地剝奪了他人的自由,類似的悲劇理應糾正。而對於那些確實犯罪且被剝奪自由的人來説,其正當權利同樣不應受到國家的侵害。
2002年,德國人蓋弗根綁架了一名兒童,由於沒有等到100萬歐元贖金,遂撕票。警方將其捉拿歸案後,認為人質仍然存活,蓋弗根閉口不言人質關押的地點,警官因此威脅將對其實施酷刑。服刑後,蓋弗根起訴該州警察局,稱恐嚇行為對其帶來心理傷害,並以人身及精神傷害為由提出賠償損失1萬歐元。法庭認為,參與審訊蓋弗根的兩位警官“嚴重侵害法律”,其賠償要求合理而判決蓋弗根獲得3000歐元國家賠償。但法庭駁回了其精神損失費的要求。
刑訊逼供所獲得的證據不予採納,是司法實踐的共識。罪犯被剝奪了自由但作為人的尊嚴尚存,更進一步説,無論是罪犯是否被冤枉,權追究司法的錯誤向國家索賠是其基本的權利。

自由到底價值幾許?國家賠償法第26條規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引發爭議最大的也正是國家賠償的數額,有人戲稱這不過是“補發工資”。從國際上來看,這個數字不失公允。在美國佛吉尼亞州,冤枉服刑每年按州平均工資的90%賠償,20年封頂;緬因州則規定賠償總數不得超過30萬美元;愛荷華周的冤獄賠償是每天50美元,每年不超過25000美元。2002年前後,110名憑DNA平反出獄的男子中,只45人得到賠償,款額由25000美元至3600萬美元不等。可以説,賠償多少受到地方政策、案件性質、律師水平的影響很大。有些“罪犯”平反後也表示了對於賠償的不滿。關押期間所承受的壓力和痛苦,絕非“補發工資”就能彌補。
恢復原狀,是國家賠償的重要內容,但這一規定只在實物和財産被侵害的情況下有效。在美國很多州的國家賠償規定中,平反獲釋人員將接受免費的大學教育和心理治療。如何幫助其融入社會,回歸正常生活,在無法完全恢復生活原貌的情況下,補充性的撫慰方式就顯得很有必要。
在得到賠償之前,美國各州政府會為平反獲釋人員消除犯罪記錄、申請獲取公共福利和子女監護權,並立即提供基本生活用品、生活費、食物和交通等,幫助安排價格合理的住房。當然,最重要的還包括政府層面的公開道歉。
1989年,紐約一女子遭到強姦,3名黑人青年被判強姦等罪名成立,真兇伏法後。3人將紐約市政府、警察局等相關機構個人告上法庭,稱誤判讓他們受到了“嚴重的永久傷害,包括7年多的監獄關押,並因此而失去自由、友誼和收入,精神和生理上的痛苦、損害、煩惱、恐懼和屈辱,以及強姦罪名引發的人格和名譽損失”,索賠每人5000萬美元。在另外一樁長達30餘年的冤案中,四名曾經的“強姦犯”獲得了美國政府1.01億美金的賠償。
涉及人身自由的國家賠償案件中,鉅額賠償金的往往源於精神賠償。政府所承擔的直受害者的接損失,僅佔很小的比例。失去自由帶來的間接的、精神層面的損失讓人們看到了國家暴力所蘊含的恐怖的力量,無論是適用英美法係還是大陸法係的國家,都贊同對這種力量的過失予以懲罰,無論到位與否這都是對權力敲響的警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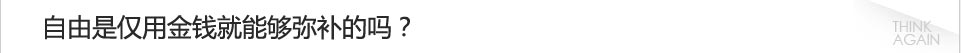
日本國家賠償法第一條規定,日本國家權力行為引起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是公務員個人主觀過錯,強調國家負賠償責任的前提是主觀過失;在瑞士,只有當公務人員的行為涉嫌違法,才能歸責與國家。
如何做出國家賠償,各國有着不同的標準。而在司法實踐中,行政手段如何犯錯並非確定賠償的主要依據。1961年,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某案件的判決中確認,既然沒有實際上的物質損害,獨生子的死亡給父親造成的痛苦也可作為後者獲取賠償的理由。該判例開了法國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先河。在前文所述的賠償金高達一億美金的案件中,由於國家對受害者自由的侵害使得他們的孩子無法享受正常的童年生活,法院判決國家對4人的10個孩子做出每人25萬美元的賠償。“補發工資”即可息事寧人?權力機關對受害者的境遇可以視而不見?一樁冤假錯案毀掉的往往是一個家庭,司法實踐的錯誤需要懲罰,受害者的心靈也許撫慰。
曾代表三名脫罪者的德州休斯頓律師沙夫特表示﹕“公平並不存在,社會仍然不認為須就錯判而承擔責任。”他指出,身陷冤獄者要面對血腥、性侵犯等煎熬,失去的也不只是時間、自由和前途。
無論定罪者是陪審團亦或法官,主觀錯判根本無法避免,法律制度最大的漏洞恰好是將其建立起來的人。自由值多少錢?事實上,對於這種不具有市場價格的物品的賠償,得到完全的補償是不可能的。一件冤假錯案,無論進行怎樣的補救,都無法令被害人回到此前的時光。漏洞造成的悲劇無法徹底彌補,但看似冷冰冰的賠償數額卻最能代表國家認錯的誠意,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吧。
“遲到的正義就是非正義”,這是一句著名的法律諺語。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他們願意走上法庭面對司法的裁決,就證明了他們對法律的一種信任,正義要實現,但不能以一種錯誤的、遲到的姿態實現。
意大利法理學家貝卡利亞在他的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中就刑罰和犯罪之間的關係説到,“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冤案積壓的時間越長,距離真相也就越遠,所積壓的社會影響就越發惡劣。法官、法律還有多少可信度,一件錯案不只給受害者帶來了災難,更令正義蒙羞,通過最大程度的彌補來重塑公民對司法的信心,雖是亡羊補牢,但好在還有得補。
生命有涯,自由無價,以有涯隨無價,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