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視網|視頻|網站地圖 |
| 客服設為首頁 |
據報道,重慶今年將推廣未成年人污點消滅等制度。在此之前,渝北區就曾試行“前科封存”制度,前來辦理封存的家長都説“不願意看到孩子帶着污點過一輩子”。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前科消滅制度為世界各國所認可,新修改的《刑法》也將前科消滅的精神正式寫入。但撫平這道青春的傷疤絕非“照章遵守”這麼簡單。 [詳細]
第282期

我國《刑法》第100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這也就意味着“受過刑事處罰”是實施前科報告制度的前提之一。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有罪的判決只能由人民法院進行,而不能由人民檢察院進行。而一般的行政處罰都不會被納入“前科”的範圍之內。前科既是犯罪者的“污點”,也是對其的警示,我國刑法規定,有前科的人在原刑罰執行完畢5年之內再犯罪的應該從重處罰。
《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總則規定,應充分注意採取積極措施,調動所有可能的資源,以便促進少年的幸福,減少根據法律進行干預的必要,並在他們觸犯法律時對他們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地處理。
世界範圍內,各國通過對未成年犯加大緩刑的適用,實行工讀學校制度、社區矯正制度、有些少管所實行的回歸教育等等方法貫徹這一理念。中山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合議庭審判長曾説,未成年罪犯在主觀上都具有作案動機單純、隨意性大、主觀惡性不大等特點。可以説,有效的教育可以促使其“改邪歸正”,且較之嚴刑峻法所付出的社會成本較低。
相比於專業技能指導等輔助措施,掃清回歸社會過程中制度性的障礙才是法治文明的切實體現。《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規定,“未成年罪犯的檔案不得在其後的成人訴訟案中加以引用”、“對未成年罪犯的檔案應嚴格保密,不能讓第三方利用。只有與案件直接有關的工作人員或其他經正式授權的人員才可能接觸這些檔案。”消滅前科制度就此確立,並成為世界共識。
《聯合國保護被剝奪自由少年規則》第十九條規定:對未成年犯“釋放時,少年的記錄應封存,並在適當時候加以銷毀”;日本1948年《少年法》第60條規定:“少年犯刑期執行完畢或免予執行,適用有關人格法律的規定,在將來得視為未受過刑罰處分”;在《刑法》修改之前,我國多地法院已經開始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除的嘗試,2011年開始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在第100條增加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免除前款規定的報告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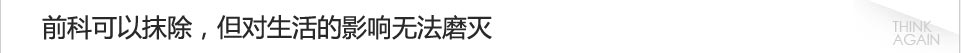
顯然,前科的消除在實踐中是存在邊界的。德國1974年《少年法院法》的規定,將未成年人刑事污點消滅的實質要件界定為:被判處少年刑罰的少年犯用無可指責的行為證明自己已經是一個正直的、不再危害社會的人。這也是很多國家制定該政策的基礎。
2009年,山東省樂陵市實行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滅”制度,其條件是:“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了犯罪並被樂陵市法院判處刑罰,且刑罰已執行完畢”的;對未成年人累犯的,不能取消其“前科”;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毒品、嚴重暴力犯罪的首要分子、主犯等主觀惡性程度較深的犯罪,也不在“消滅”之列。對於性質惡劣,主管犯罪意識強烈的未成年人來説,無條件的前科消滅只能助長這類人再次犯罪的慾望。
但顯然,前科消除的精神與我國部分民事、行政法律是相互衝突的,國家機關和單位仍然有權調看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並在就業、入學、入伍等方面予以限制,例如,教師法、會計法分別規定了“因受過剝奪政治權利或故意犯罪受過有期徒刑以上處罰”,“喪失教師資格”、“不得取得會計從業資格證書”;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分別規定: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得擔任法官”、“不得擔任檢察官”、“不得擔任人民警察”。
此外,公安部門的《重點人口管理規定》中開具有無犯罪記錄證明的規定以及有關戶籍管理的規定;教育部門有關招生、資格審查的規定,等等。我國的法律中並沒有銷毀犯罪記錄的相關政策,犯罪即為一輩子的“污點”。
根據貝克爾提出的罪犯的“標籤理論”,“一定的社會群體通過制定法律規範而確立什麼是不軌行為,並通過對特定的人應用這些法規,給他們貼上標籤並將其作為社會的局外人”。這也就意味着,此人犯罪者的形象會影響周圍人對他的看法和態度,而他自己也會按照他人的想法重新定位自己——我是一個有罪的人,我所受到的待遇和別人不一樣。
某法院院長認為,“當他們刑滿釋放,帶着有‘犯罪前科’的標籤走上社會後,升學、就業很容易碰壁,常常有一種‘破罐子破摔’的心態。”二次犯罪也成了很多人再次做出的錯誤選擇。犯罪後心理如何矯正,這是政策解決不了的難題。

由於立法者是經由人民選舉産生的,因此每項法律所代表的都是人民的意志和態度。以恰當的方式原諒未成年人犯罪,已經成為了社會的共識。但它所指出的僅僅是一條回歸社會的路。
克林頓總統曾簽署《梅根法》,要求危險的性騷擾者和強姦犯在出獄後遷入某社區時,地方官員應向這個社區公開其犯罪的資料。法學教授王琳在文章中提到了其學生對於《梅根法》的看法,其中有半數同學反對;而當問題變成“假如有一位強姦犯出獄後要遷入你所居住的小區,你贊同地方官員預先向小區居民公開其犯罪記錄嗎?”的時候,贊同者接近九成。公眾對於侵害他人自由的行為有着自己的判斷,這種具體的情況是制度無法也無需考慮在內的。重新融入社會,回歸者自己、全社會都需要付出很多。
2011年11月11日,日本法務省推出年度《犯罪白皮書》,一組數字表明,20歲以下的少年犯從“少年院”出來以後,大約40%的人還會重新犯罪。少年犯再犯罪是全世界青少年教育的難題,前科消滅雖然利於青少年回歸社會,但其同樣容易起到縱容犯罪的作用,善意的規則被富有惡意的犯罪分子鑽了空子,才是類似制度最大的隱患。
據《深圳晚報》報道,“少年犯群體大部分的文化程度很低,尤其缺乏法律意識,很多人在犯罪的時候都不知道是觸犯了法律。到了高墻之內才明白過來。”一個人誤入歧途不能完全歸咎於社會,但減少身邊的犯罪示範,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卻是每個公民應盡的職責。社會的正能量可以糾正他人缺乏自律的行為,預防犯罪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人感受到生活的希望。
不管怎麼説,有前科的未成年人畢竟侵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但懲戒總歸是有盡頭的,給他們貼上終身的犯罪標籤,無異於最不人道的嚴刑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