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視網|中國網絡電視臺|網站地圖 |
| 客服設為首頁 |
By 雲也退
“第一修正案不保護帳篷,它保護的是言論和集會。”
10月,紐約市市長布盧姆伯格就“佔領華爾街”運動説了這麼一句話。在奧巴馬&&表示同情以來,布盧姆伯格也加入了默認抗議者有理的美國高官富紳的一員。他也像總統一樣,談到了“最好的做法是不要掀掉抗議者們的帳篷”,雖然理由比較冷血:這將動用過多的警力。
將來,當人們給“佔領華爾街”蓋棺定論時,會不會認為它取得過“階段性勝利”呢?
對祖科提公園的抗議者來説的確如此:首先,不必管敵人的心虛退讓,網民、報紙讀者和電視觀眾的注意力就是他們的勝利,他們的口號和行動,無疑在擁有鉅額財富與製造罪惡的體制之間畫上了堅硬的等號;其次,儘管第一修正案的確不保護帳篷,但是帳篷就是公共空間的言論表達,傳遞了明確無誤的信息,這個信息,比之前在羅馬、倫敦、利物浦、布裏斯托等地用磚頭、啤酒瓶、汽油、棍棒表達的情緒要理性而有力得多;最後,11月16日的形勢拐點讓這一階段的時間下限得以明朗:在以紐約為首的各個捲入這場大串聯的美國城市,當政者不約而同地發動了肅清帳篷的行動。
這很可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若是失去了自己的標誌性景觀,而又未能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比如“散步”之類),“佔領華爾街”必將很快從公眾原本就極難聚集的注意力中消失。不過,對那些持傳統左翼立場或懷有那種情結的知識分子而言,這場運動到現在為止,已給他們留下了足夠重要的啟示。
1
經歷過漫長的冷戰和“歷史的終結”之後,天性再樂觀的革命家,怕也不敢輕易斷言資本主義已經露出行將崩潰的端倪了。“佔領華爾街”之最值得注意之處並非它的意圖,並非那些屢屢出現在網絡視頻中、叫嚷“我們反對的是這個體制!”的人的象徵意義,而是它採用的方法:抗議者們開發了一種政治表達的新形式,把對苦難的敘述用和平的、幽默的甚至狂歡的方式來裝載,每一個人都把“99%”作為他們的Logo。在這面旗幟下,他們持續向不特定的人群開放,接納新成員,而每一個新成員的加入,都是對一個捲入全球貿易網絡的無産階級化的大眾業已形成或正在壯大的有力注腳。與之相對應的,美國是這個全球貿易網絡的中心舞臺,華爾街則象徵了各種不平等現象的策源地。
這個時候, 即便抗議者們只字不提,馬克思的幽靈也會在理論家、觀察家們的筆下和頭腦中接受鄭重的招魂禮。
特裏� 伊格爾頓( T e r r yEagleton)今年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駁難體的新作:《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沒想到此書出版不久,倫敦全城(至少在主流媒體眼裏)毫無徵兆地打砸搶蜂起,然後蔓延到利物浦、利茲、伯明翰、布裏斯托等大城市,以至於英超足球聯賽都受了株連,托特納姆熱刺隊至今還少打一場比賽;緊接著的便是祖柯提公園支起的營帳。伊格爾頓也想不到,這本書會讓中國的出版商如獲至寶,當作進獻給執政黨的壽禮。
平心而論, 對讀者而言, 單單接受這份急就章式的辯護狀所給出的結論意義不大。但是,我們可以借此了解,馬克思的思想資源對敏感於動蕩的全球環境的西方左派學者而言,如何構成一種持續的激勵。伊格爾頓堅稱,馬克思絕不是什麼唯恐天下不亂的煽動家,也絕非一意孤行地要給資産階級一點顏色看看,相反,馬克思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在推生産力、積累物質財富方面的歷史功績,就反抗而言,他也支持工人參與議會選舉,謀求在體制內更大的發言權。
伊氏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種種的陰鬱指控,表明他“對歷史的極度悲觀”,而他提出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其是在挑動一堆人拔刀拔槍地反對另一堆人,不如説是反映了其對未來的樂觀。一如他在歷史必然和主觀能動之間轉圜自圓一樣,馬克思嫻熟的辯證法,始終為社會向著公平方向的改進留住了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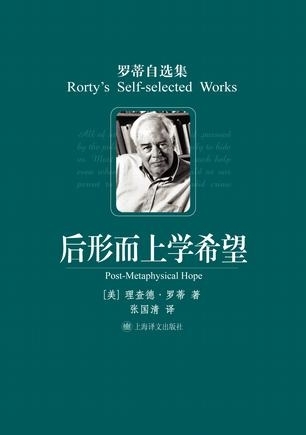
可以斷定,眼下發生在美國的事能給伊格爾頓這樣的學者帶去何種靈感。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後形而上學希望》裏提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激發國際左派集體想象力的一股力量徹底消失了,這股力量繼承了馬克思的一個思維前提(由黑格爾開創),即“模糊了理解世界和知道如何改造世界之間的差異”。羅蒂在這裡暗示,或許承認不知道自己怎麼改造世界,才保住了改造得以實現的可能;這也是伊格爾頓必然贊同的觀點。
與此相應,“佔領華爾街”的主要威力——如很多觀察家所指出的——恰恰來自一種“無”性:無中心、無綱領、無意識形態、無具體訴求,只有一些自覺遵行的、保證運動不給媒體落下口實的基本紀律,甚至就連參與者自己,也不知道它將向哪走去。一位署名阿尤納�阿達(Arjuna Ardagh)的抗議者寫下了這樣的評價:“這太棒了,當一個運動並不圍繞某個中心來組織,它召喚的就是人們共有的常識心和正義感,而不是對一項教條的效忠。”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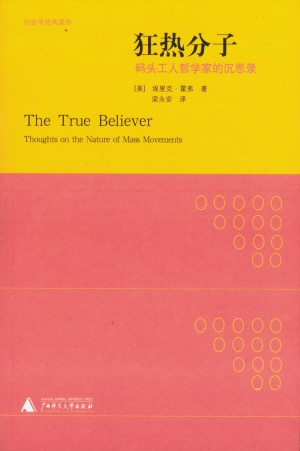
按傳統的群眾運動理論,明確的指向、美好的藍圖、卡裏斯瑪式的領袖加上一種作為最大公約數的仇恨情緒,方能激發出參與者內心源源不斷的自豪感。在《狂熱分子》這本名作中,有“碼頭工人哲學家”之稱的美國人埃裏克�霍弗(Eric Hoffer)斷言:“一般而言,一個目標具體而有限的群眾運動,其積極階段之持續時間,比一個目標朦朧而不確定的群眾運動要短。”他以布爾什維克和納粹為例,認為這兩股勢力所發起的群眾運動“追求的是完全團結和無私的理想社會”,因此才能把“不斷革命”的模式給固定下來。
很顯然,受制于所處的時代,霍弗的論述集中在那些有若干領袖(或他所謂的“言辭者”)&&的宏大設計型變革上,他沒有考慮到,“目標朦朧而不確定”可以有更多的表現形態——例如,用“佔領”而不是“抗議”、“砸爛”、“打倒”來宣説一種否定性的集體情緒。
“Occupy”一詞,讓人聯想到戈達爾等人的電影裏,那些停留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觀眾卻不知其為何在那裏的路人。抗議運動的參與者們偏偏自豪于自己的不作為,或者做一些與抗議似乎無關的事,如集體做瑜伽之類——這會讓霍弗在墳墓裏冒出一身冷汗的。
在這個意義上,露營的人們走在了紙上談兵的知識分子的前面。當年羅蒂替左派知識分子憂慮,他説,這些人瀕臨放棄這樣的幻想:“與同胞相比,我們知識分子特別擅長于在思想中把握我們所處的時代。”羅蒂實誠地説,作為一個夾在左右兩翼之間的人,他看到了海德格爾所預言的形而上學終結的危機:一個虛無主義荒原的開始,在那裏,資産階級的自由和幸福將普照人間的價值觀,而同時,那些善於從偶然中提納必然的知識分子將變得無事可做
這番悲觀的論調建立在如此的事實上:知識分子缺少一套元敘事話語,可以取代馬克思主義來描述當代資本主義的現狀。這個資本主義一面籌措資金、組織生産以推動世界運轉,一面繼續盤剝無産者,把大量第三世界勞動力變成為自己的貪慾服務的奴隸——它已經捂住了知識分子的嘴,我們無法在它早晨九點做業務報表時送上茶和咖啡,而在夜裏十二點它關上門喝嫖妓的時候去砸它家的窗玻璃。用羅蒂的話説:我們無法用“資本主義”一詞來同時指涉“市場經濟”和“所有當代不公正的根源”。
而當運動發生之後,被捂住嘴的成了華爾街的金融家們。索羅斯的口頭支持(或者説賣乖)並不太出人意料。他説,最令抗議民眾憤怒的還不是用納稅人的錢救銀行,而是已經陷入困頓的銀行還讓執行主管領取高額紅利獎金——這是看得見的不公,所以,“我覺得我可以贊同他們的看法”。相反,左派學者裏向來極具人望的齊澤克跑去演説,大談“這個世界肯定是有問題的”,卻露出一根機會主義的尾巴來——如果這個運動當真需要什麼思想和精神上的領袖,需要演説家和煽動家,恐怕早就八抬大轎,去搬他老人家出山了。
不作為的另一個側面就是無訴求。“你們要什麼?我們做個交易吧!”這種用來安撫罷工的慣有的恩賜態度,抗議者根本不給華爾街的富豪們以表演的機會。沒有訴求,此刻要比“把舊制度打個落花流水”聽起來更加有力。而他們的堅持,也讓上來就投以冷眼的觀察家們(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抗議要有抗議的樣子,比如,你要列出想讓政府採取哪些措施,來避免奧巴馬新政被右翼勢力肢解,或者舉出新政中需要修改的內容,或者告訴執政者,人民希望他們在就業、醫保、銀行監管方面做些什麼)不得不一個個調整最初的看法。
這是一次革命還是普通的暴亂呢?凡爾賽宮中的路易十六困惑到。阿達在他的博文裏説:我們希望它變成一場不一樣的革命。
3
保守派一邊的人,大量的共和黨人包括總統候選人,都把“佔領華爾街”鄙夷為與“茶黨”相對應的激進左翼活動,一個“插曲”。不過,很多觀察者所指出的令人嗟呀的多元性,是這個所謂的“插曲”的價值的體現:儘管整個運動沒有明確的訴求,但參與者的怨氣來自各個方面,有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負擔過重,有的是受歧視的少數族裔,有僅僅是家裏境況不好,自己又“擔心”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就舉著牌子往“99%”的隊伍裏一站。有警察穿著制服加入了抗議者的人群;有海軍士兵安營紮寨;有猶太人,也有穆斯林;公交車司機和消防員都戴著讓人一望便知的工作帽。
這種多元性裏當然包含為數不少的挾私分子。例如在民間不怎麼受歡迎的工會,就趁機到現場去招募新成員,物色伶牙俐齒的發言人;流浪藝人並沒有興趣與抗議者們長期同在, 只是習慣性地湊個熱鬧而已;一些人數極少的民間教派也看到了機會。《紐約時報》刊發了馬克� 奧本海默( M a r k Oppenheimer)的文章,他觀察到,有宗教信仰的抗議者們在各自的營帳裏舉行敬拜儀式(例如猶太教徒的贖罪日齋戒),基督教抗議者還組成了布道小團體。但是,小團體之間並不像當年法國“五月風暴”時的馬克思主義小組一樣,個個都號稱自己掌握了革命的鑰匙,相反,在長居戶外、共同露營的環境下, 他們友好地交換彼此的信仰、飲食和日用品。假如這種奇特的現象普遍存在,甚至如奧本海默所説,已經在遠至多倫多的抗議者群體之中發生,那麼,我們真的沒有理由再像個鄉願似的去懷念街壘和大字報。
《紐約時報》畢竟是立場偏左的。就算沒有政府的武力彈壓,抗議運動的兼收並蓄,事實上也埋下了它從內部瓦解的危險,而且,這種可能性只會隨時日遷延、陣容壯大而升高。

理查德� 羅蒂的《偶然、反諷與團結》,從一個角度上可以看作是對俄國革命式集體運動徹底絕望後的反省。書中的核心觀點是:不要企圖讓所有人都停止私人的規劃,一同去抵禦公共的危險;一個人(這話又是説給知識分子聽的)所篤信並潛心追求的、比他自身更偉大的東西,例如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並不必然地與他對別人所承擔的道德行為相干。
拿到眼下的事實中來説,就是你把你的帳篷勻給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或者隨便哪個外來客,並不意味著你就和他對同一個剝奪了你們的居住權的資産階級敵人有了共同的、堅不可摧的立場和態度。
像一個被炮彈轟掉一條腿的角鬥士一樣羅蒂有些惡狠狠地把那些知識分子的冷兵器——本質主義和形而上學——扔在了腳下,而代之以從尼采等人那裏得來的歷史偶然性。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暫時的團結,這種為赤誠的自由主義者所傾心的景象,純係出自偶發,而一旦將其形而上學化,仿佛有貫注其下的人性本質做依託,將來就要遭受兩難或多難的困境。
這種警告不是沒有道理的。當你同時隸屬於一個宗教團體(儘管也是抗議性的),又隸屬於一個大的政治抗議團體的時候,你勢必會負有兩種以上的義務,大團體的道德義務和小團體私人承諾之間,難免會有發生衝突的時候。你怎麼知道,你和我是因為什麼而團結,你和我又可以團結多久?
羅蒂只滿足於做半個尼采——他悲觀于現世,卻並未因此狂歌五柳前;與他形成對照的,是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他的《希望的空間》是一本格調奮勇的書。在書中,他指出了一個強悍的任務:在資本主義工廠消失或不穩定、永久性工人組織變得困難的條件下,我們如何既不走回列寧主義的傳統左翼先鋒老路,也不求諸左派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先鋒,來組織政治集團進行鬥爭。
哈維描述了在他的家鄉巴爾的摩,一個由教會發起的、擴及全城範圍的為爭取最低生活工資的運動如何持續存在:它不以傳統的勞動組織模式來操作,而是非常先進地以適應新環境的方式運行。哈維説,這個運動融合了種族、性別、階級所關注的問題,其成功的經驗之一,正是在“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社會階層”之間實現了同盟。哈維把自己的研究定性為探索“烏托邦機遇”,這當然不是什麼關於人間天國的迷夢,而是事關新的組織形式的形成。在哈維看來,反資本主義的運動可以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髮現,問題就在於如何去組織,去綜合其力量。
哈維的書中沒有關於“團結”的考量,這個詞未免過於書生氣了。但是,這不妨礙把團結與否看作估量一個群眾運動的生命力的最直觀的標準。
最低生活工資運動形成的同盟畢竟還走不出巴爾的摩,而“佔領華爾街”卻撒豆成兵一般地擴散其規模。聰明的組織者們似乎知道應該怎樣把零散的手指攥成拳頭。看到專為捱冬所準備的16�16英尺的帳篷和11�11英尺的帳篷搬進祖柯提公園的景象,你會感到,這些抗議者們好像已準備好了要接受氣溫和凝聚力的雙重試煉。
4
左翼沒有樂觀的理由,資本主義早晚要用無産階級的營帳裝點自己的風景。對不知去向何方的抗議者們而言,營帳存在一天,試煉便將進行一日。要推進一場政治運動,在自己的陣營裏“求同存異”殊非易事,必須指靠每日迫在眉睫的行動;而誰也不敢説,一對水火不容的私敵能在營火晚會裏前嫌盡棄,干戈玉帛——若真能如此,馬克思預言的理想社會也不至於一再延期,成為一種無法證偽的政治彌賽亞主義。正是基於這一點認識,理查德�羅蒂否棄了康德對“我們可以指望共同人性”的預設:“如果我們把道德進步的希望託付給了同情心,那麼我們實際上把它們託付給了恩賜。”
儘管如此,羅蒂依然承認《共産黨宣言》的魅力:__“對於社會正義的希望仍然是一種有價值的人類生活的唯一基礎”,他也承認,“馬克思主義者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確的:核心政治問題是富人和窮人的關係問題。”這便是那些一屁股坐下來安營紮寨的人,在這個秋天小心翼翼地測探的社會共識——最壞的測試結果,也不過就是卷鋪蓋回家各找各媽。
然而,形勢的進展很可能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在這個芝加哥的貧民區與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窟看起來不分彼此的同一化時代,不滿的不僅僅是那些自封的“99%”,同樣,在這個任何底層反抗都可能砸掉其他無産者飯碗的全球化大生産時代,祖柯提的人們得到了免費的食物、日用品、書籍、醫療和法律服務。大多數美國民眾對這一抗議並無半點關心,積極響應的只是少數人,但是,這種待遇,畢竟是羅馬和倫敦那些被公共輿論一面倒地痛斥為“不知羞恥”、“踐踏法律”的暴徒無法想象的,也是曾幾何時,從別人手上奪下索尼相機、砸壞路邊的豐田汽車的中國反日分子們無法想象的。
它的“無欲則剛”是策略,也是一種詩學。詩學的功效是點燃人們的想象力。因為“無欲”,所以它也沒有邊界;因為“無欲”,所以它並不像上世紀名聲已壞的試驗者們那樣,對著“不斷革命”、官僚建制、利益集團等一碗碗苦湯狐疑不決。
我還記得,十二年前的那個五月,許多人只是“佔領”了美領館外的空地,但他們把自己的行為命名為“抗議”和“打倒”。也許是知道第二天就要各奔前程,所以心心唸唸畢其功於一役吧。在這場旌麾獵獵的“鹹與”中,偶爾也會響起因互相推搡引來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羞憤叱喝,讓我想起奧威爾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裏寫到的,那些頂著馬克思、列寧、盧森堡、托洛茨基的頭銜、互相以鄰為壑的左派營壘。
羅蒂是對的:不存在一種形而上學的“核心自我”,可以把人,這群嚶嚶嗡嗡的政治動物牢固地、長久地攥到一起。知識分子壓根就不應該往那個方向去想。
相信自己有義務使未來比現在更可取的知識分子們,可以持守的只是想象力。在“列寧主義的終結、哈韋爾和社會希望”一文中,羅蒂寫到了1989年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那個時候,就連哈韋爾本人,都不知道那場革命
將如何進行下去,他帶著個戲劇家的頭腦,“似乎準備全力以赴地致力於用沒有根據的希望取代理論洞見。”他像一個半醉的夜歸者,一個頹廢的人,這種頹廢來自於他唯一確知的東西,那就是他自己的局限,就是個體的主張,只是恒河沙數的細小瑣屑之一,只有被拼湊、被匯聚、被滾雪球的可能。然而,就在拼拼湊湊、錯進錯出之中,布拉格的人們放棄了杜布切克,用充滿了偶然與反諷的個體抉擇,將國家撥到了一條現在看起來最優的軌道上。
當工人階級果真按馬克思的理論揭竿而起、反對培養他們的體制時,他們會不會樂意接受一個被歷史安排好的“掘墓人”角色?自由與必然的辯證讓理論家感奮,卻未嘗不會讓實踐者躊躇。如果俄狄浦斯預先知道自己要去弒父,他會去埋怨拉伊俄斯,還是去埋怨為他刻下了悲劇結局的索福克勒斯呢?
我想過這個問題。所以, 我認為現在就嘗試在左派運動的地形圖上繪出“佔領華爾街”的位置必將大錯特錯。一種取代了政治神學的希望詩學(不管它是不是被冠以“馬克思主義”)不允許知識分子再犯這樣的愚蠢。毋寧説,當年羅莎�盧森堡在獄中引以自我激勵的那句新教改革家烏爾裏希�馮�胡頓的話“我挑戰過了!”,更接一個堅定的反資産階級人士應有的精神狀態。
這是一條不歸路,一條在《新共和》的評論員沃爾特� 夏皮羅(Walter Shapiro)眼裏只有給媒體充實談資的價值的路。他挖苦説,在“常規戲碼”遲遲未開鑼之前,“佔領華爾街”還只能是一場鬧劇:“我也認為,嚴肅的記者們一直在等待一些人跳出來憤怒地咆哮,控訴華爾街的寡頭們成天拿著年金開懷大笑的樣子。”他沒有看到那非常規的戲碼早已開場,或者,只是不願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