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視網|視頻|網站地圖 |
| 客服設為首頁 |
一張金額高達2151萬的天價罰單,讓李清一家高呼“十輩子也賠不起”。李清並非什麼巨商富戶,他只是一名販賣假名牌羊毛衫的小商販。據他自己説,在被捕之時,假羊毛衫不過讓他獲利1萬元。法院做出罰金判決的依據則是服裝吊牌上的價格。李清認為自己很委屈,而這兩千萬的罰單在很多人看來更是荒謬無比。[詳細]
第170期

面對兩千余萬元的罰單李清選擇向內蒙古高級法院提起上訴。據最新報道,鄂爾多斯中級法院的一審判決已被撤銷。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其中最為關鍵的證據就是天價罰金的來源——李清到底賣了多少錢的假羊毛衫。據《廣州日報》報道,一審時,李清的代理律師南新丹提供了光盤和淘寶網上買賣的記錄,證明毛衣的實際銷售價格大約每件是130元。但公訴人認為這只能證明網店的銷售價格,不能證明這是實際銷售價格。而李清又告訴南新丹,公安曾扣押了其兩台詳細記錄了實際售價的電腦主機和賬本,但南新丹發現賬本和電腦沒有移交給法院。李清的辯護律師王福奎認為這是本案最大的疏漏:“對實際銷售的446件羊毛衫價格,應當逐一查清其平均價格才能用來計算非法經營數額。但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同樣涉嫌證據不成立的還有偵查機關進行搜查、審訊的時間。據新華報業網報道,相關案卷顯示,公安機關從2010年12月15日17點20分開始搜查假冒羊毛衫,2010年12月16日7點30分結束。但訊問筆錄又是在鄂爾多斯市東勝看守所,訊問的時間是2010年12月16日10點20分開始,11點16分結束。也就是説管理搜查筆錄、扣押物品清單及訊問筆錄偵查機關涉嫌造假。
從地圖和旅行時間可以看出,從湖南長沙到呼和浩特市乘飛機需要2小時,呼和浩特市到鄂爾多斯市汽車最快也要3個小時,而且郴州市距離長沙市有300公里之遙。據此,即便是辦案人員毫無縫隙地搭乘交通工具從郴州前往鄂爾多斯,在案卷提供的時間裏,是絕對辦不到的。
涉及“跨省追捕”也是本案的一大看點,據報道,李清的妻子説,當時是一名郴州當地警察同兩名鄂爾多斯警察一道,對其假羊毛衫進行的查處,並將夫婦二人帶往鄂爾多斯羈押。李清的代理律師王福奎稱,鄂爾多斯公安局涉嫌程序違法。
我國《刑訴法》第24條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轄。”王福奎認為,犯罪地是指犯罪行為發生地,李清的犯罪地在郴州市北湖區,鄂爾多斯既不是犯罪地,也不是犯罪行為發生地,也不是犯罪結果發生地。同時,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産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侵犯知識産權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因此,鄂爾多斯公安局沒有立案偵查權。

《刑法》第213條規定,犯假冒註冊商標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因李清案的假冒標誌近3萬套,查獲假冒註冊商標的羊毛衫26187件,涉案金額達6萬元,獲利達1萬元。以此為據,法院按《刑法》的“情節特別嚴重”規定,以上限為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標準,處以5年監禁並處罰金,這應該説于法有據。
李清一審被判犯有“假冒註冊商標罪”。辯護律師南新丹認為,這是“案件定性錯誤”,李清應當被定為“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根據《刑法》規定,簡而言之,“假冒註冊商標罪”是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則是銷售明知是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
對於李清來説,在他將假商標縫製在“白坯衫”上時,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就發生了,而銷售假貨則構成“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但辯護律師南新丹認為,“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的行為和銷售、使用偽造的註冊商標的行為是分別獨立的行為,各方沒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李清的目的只是銷售,與商標的製作、購買、銷售和縫製並無關係。
回到案件最為吸引人的地方——2100余萬元罰金。據報道,李清所購入的吊牌,假冒“鄂爾多斯”價格有1680元和2180元兩檔,分別是17403件和4351件,而標價968元的假冒“恒源祥”則有4433件,吊牌價總額達到4301.3364萬元。這正是“天價罰金”的基礎,鄂爾多斯中院以這一金額的一半判做了李清的罰金。
面對千萬級的罰金,李清則認為,罰金的認定應該以實際銷售、獲利金額為基礎,而不是人們印象中“價格可以隨便標”的吊牌價。而依據相關法律,當部分假貨售出時,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經營數額,可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産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很顯然,鄂爾多斯市中級法院選擇了罰金較高的前者作為判罰依據,這也直接令李清的妻子感嘆“十輩子也還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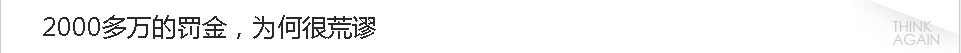
我國《刑法》規定,罰金屬於附加刑的一種。監禁等主刑才是對犯罪行為進行懲處的主要方式。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和靜鈞評論稱,罰金是行政手段徵收的民事處罰,本質屬於“債”的關係,具體數額取決於被告所處的社會經濟水平與被告本人“履約”能力。此前,湖北婦女陳少紅的餐館被認定違規裝修,且逾期未繳納罰款,被法院裁定執行總計14萬元罰款。由於無力支付,陳少紅選擇了服藥自殺,當地政府最終認定罰款額不應超過2000元。
我國《刑法》第52條規定:“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這種以犯罪情節為唯一依據來確定罰金的數額,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病,因受刑人的貧富不均而可能造成的罰金刑執行的實質上的不平等。在此案中,對於並不富裕的李清家來説,監禁五年與罰款2000萬相比孰輕孰重並不難判斷。法院作出判決的目的,未免顯得本末倒置。
恰如前文所説,法院在做出一審判決之時,在較輕和較重兩種量刑標準之中,選擇了較重的量刑。法院僅從吊牌價簡單乘以查獲的襯衫數量,得出一個從常理與常情上均不可能的天價經營額,然後簡單地取其一半金額作為罰款的最終數額,這顯然是草率的。而更加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法院對於關鍵證物——儲存有銷售金額的電腦,並未進行取證,僅憑單方面的指控便定下了犯罪金額的判斷。
有人評論到,這種推斷明顯是一種罪重推定,實際是一種變相的有罪推定,這既與當今重視保護個人權利的時代精神不相符,也與我國憲法和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相背離。
商在年初,一場“天價過路費案”引人關注,河南一農民時建鋒使用兩套假軍車牌照,在8個月的時間裏,免費通行高速公路2361次,偷逃過路費368萬餘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到再審,賠償金額被認定為49萬餘元,如此巨大的反差才是人們關注此案的真正原因。《法制日報》評論稱,“也正是“天價過路費”引發了人們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
有網友稱,“若是按照標牌價格定賠償,那達芬奇應該被罰多少錢呢?還是133萬?”《廣州日報》評論稱,現在社會上有人抱怨開發商違規或油企污染環境罰了數萬元就算數,而對農民違規卻開出“天價”罰單,從這樣的抱怨可以看出,“天價罰單”傷害了法律的公信。
天價罰單固然很荒謬,而“天價過路費”一案也似乎展示了這張罰單未來的命運。恰如很多當地商販在採訪時説的那樣,市場對於假傢具假奶粉假食品的生産者的查處,怎麼總是隔靴搔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