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標題:

英國歷史學博士李愛德和朋友馬普安重走長征路。五洲傳播出版社供圖

9月30日,國家外國專家局的外國專家和親屬來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英雄史詩 不朽豐碑——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主題展覽”。新華社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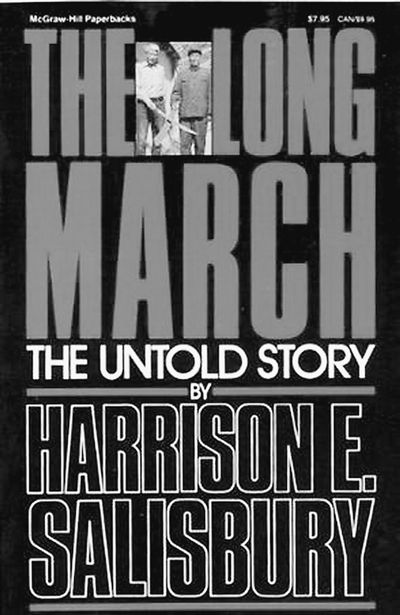
哈裏森·索爾茲伯裏所著《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英文版。資料圖片

武大衛展示他的藏書之一《毛澤東詩詞》,他非常喜愛這本書,在其中夾了不少筆記。本報記者 韓曉明攝

甘肅會寧縣城西津門,1936年10月2日,紅一方面軍騎兵奔襲會寧,首先攻開此門,打開了勝利通道。隨後,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後與紅一方面軍在會寧、將臺堡(今寧夏西吉縣將臺鄉)勝利會師,舉世聞名的紅軍長征勝利結束。1958年,西津門改建為紅軍會師樓。資料圖片
80年來,紅軍長征早已為外國記者、作家和學者所廣泛報道、記述和研究,紅軍在長征中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和鬥爭精神超越時空,走向世界。長征精神已成為激勵世界人民為了理想和信仰克服困難、堅持前進的巨大精神動力,正如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所説:“長征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徵,人類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人類勇氣與怯懦的搏鬥”
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們用飽含深情的筆觸,將真實的長征介紹給世界。斯諾衝破重重封鎖,來到陜北根據地,對紅軍進行採訪。1937年10月,斯諾在英國出版了根據採訪手記匯集而成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第一次向全世界全面報道了長征的經過,一個多月就發行5版,並很快被譯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種文字出版。斯諾稱長征為無與倫比的史詩般的遠征,他充滿激情地寫道:“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
“大地的女兒”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用1/10的篇幅,以生動、細膩和雋永的筆觸,刻畫了紅軍長征,向世界人民展現了長征這篇英雄史詩。她認為,“事實、數字和一路上千山萬水的名稱,都不足以説明紅軍長征的歷史性意義,它們更不能描繪出幾十萬參加長征的部隊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以及它們所遭受的苦難。”紅軍經過長征,雖然“瘦的只剩下骨頭架子”,但它“稱得起是世界上最頑強、最結實、最有政治覺悟的老戰士”。美國學者裏奧·胡柏曼和保羅·史威齊都稱讚“長征”章節是本書“高潮”,他們認為:“與長征比較起來,漢尼拔跨越阿爾卑斯山在‘歷史的小劇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侖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災難性的失敗,而長征則是最後的勝利的前奏曲。”
斯特朗曾6次來到中國,報道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她的名字與中國革命鬥爭歷史密切相連。在《中國人征服中國》一書中,她專門介紹了“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英雄史詩”——長征。她寫道:由於“為中國的獨立而戰”的建議“石沉大海”,所以紅軍“決定採取現時代最富有戲劇性的勇敢行動,進行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遠征。”她正告讀者:紅軍借長征宣傳了抗日,實現了民族團結,“在長征途中,紅軍始終在宣告,中國必須為抗日戰爭的到來做好準備。”紅軍來到西北就是為了“向十一個省的人民宣傳民族團結的必要性。”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澤·施瓦茨,1907年生於德國,是一位堅定的反納粹戰士。1935年,她在倫敦與王炳南結婚,並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名字——王安娜。轉年2月,王安娜隨王炳南來到中國,將青春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1964年,她把在中國的“自我實際的體驗”,寫成了回憶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傾聽紅軍戰士所講述的“許多詳細的情況”,使她感到長征是“無與倫比的現代奧德賽史詩”,在她看來長征是“人類的勇氣與怯懦、勝利與失敗的搏鬥。”她特別向讀者講:長征“這一行動要戰勝敵人和惡劣的自然條件,需有堅定不移的勇敢精神。”
“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徵”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外國學者對長征産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出版了一系列專著。西方世界最早的長征著作,是由法國哲學家布瓦1957年出版的《長征》。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中國與西方關係迅速升溫,大量著作開始出版,塔頓的《毛的長征曆險記》、埃德蒙茲的《毛澤東的長征:人類大無畏精神的史詩》、溫徹斯特的《毛的足跡》、弗裏茨的《中國的長征:危險的6000英里》;1963年,日本學者岡本隆三齣版了《長征——中國革命進行考驗的記錄》,隨後他又出版了《中國革命長征史》和《長征秘話》等著作。蘇聯學者西基梁斯卡婭和尤裏耶夫分別於1962年和1986年出版了《中國紅軍的長征》兩本同名的著述。上世紀90年代,西方學界又陸續推出了美籍華人學者楊炳章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日本賓戶寬的《中國紅軍——困難與險峻的二萬五千里》以及法國迪皮伊的《毛澤東領導的長征》等著作。
迪克·威爾遜是知名中國問題學者,曾任《中國季刊》主編,他出版了《長征:中國共産黨求生存的史詩》和《毛澤東的長征》等兩本著作。在《史詩》一書中,威爾遜不滿足於前人以新聞紀實的方式簡單記錄和描述長征,他從歷史性、傳奇性和象徵性這三個方面對長征進行了研究,他強調長征是“生存的史詩”,是“中國人民重要的精神財富”,他站在人類精神的高度講:“長征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徵,人類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1984年春,讀了《西行漫記》而“被長征的重大歷史意義所吸引”的美國作家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偕夫人夏洛特沿紅軍長征路線進行了採訪,並完成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索爾茲伯裏不顧年邁體衰,心臟病發,堅持從瑞金走到吳起鎮,行程11500多公里,他認為:“只有走過了這樣的路程,只有吃過這樣的苦,才能理解紅軍長征的偉大。” 同時,他還訪問了參加過長征的黨政軍領導人和許多紅軍老戰士。和許多作者一樣,他盛讚長征在人類歷史中的巨大意義,“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跡”,長征“是一次充滿了集體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希望的舉世無雙的行動”。在書中,他還闡述了許多自己的深刻洞見。對長征在革命年代的價值,他寫道:“長征是一篇史詩。這不僅是因為淳樸的戰士及其指揮員們所體現的英雄主義精神,還因為長征實際上成了中國革命的熔爐。”索爾茲伯裏敏銳地觀察到了長征精神在中國改革開放這一“新長征”中的重要價值,“長征體現了勇氣、毅力、智慧和艱苦奮鬥,這和中國現在的現代化過程所需的勇氣、毅力、智慧和艱苦奮鬥的精神相同,因為兩者都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奉獻。” 他告訴世界,長征“所表現的英雄主義精神激勵著一個有11億人口的民族,使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
和索爾茲伯裏的相識“最終促使”楊炳章下決心研究長征。1990年,他在美國出版了《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這本書被認為是“一本嚴謹的、全面研究長征”的學術性專著,通過“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的模式來解釋,長征途中中國共産黨“在地域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作者基於地緣政治的視角研究長征,他指出:長征是共産主義運動“從中南地區到大西北的一個必要的總體轉移”,從此,中共進入了“中國的政治舞臺的中心”,同時,華北、西北“沒有被觸動過”的鄉村社會,也為中共“保留了一種高度的政治潛能”。
“克服落後東西的必要因素”
在海外學界出版的許多黨史、國史和領袖傳記中也就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業績”,做出了經典性的描寫和闡述。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專門談到了長征,他將長征比作《聖經》中的“出埃及記”。他認為長征有兩個重要結果,一是為中共“找到一個新的根據地”“安定的地方整頓自己”,另一個是“促進了新的領袖的出現”——毛澤東,長征也為他找到了“最親密的同事”——周恩來,這個“有偉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
研究新中國史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及其之後發展》就強調,“長征是一個充滿政治上和心理上重要意義的事件。”在政治上,毛澤東通過長征重新獲得黨和軍隊的領導權,把革命隊伍帶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地區,這裡可以“實現他們要對日本人作戰的誓言”,從而“實現愛國和革命的目標”;在心理上,長征給了人們以極其重要的希望和信心,也孕育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奮鬥不息、英勇犧牲、自我克制、勤奮、勇敢和無私”等美德。“傳記天才”特裏爾在《毛澤東傳》中也突出強調了長征的心理意義,“一切嶄新的社會制度都是起源於理想”“共産主義中國就誕生於長征的汗水、鮮血和冰雪之中,它激發了戰士們對新社會的渴望,也培養了他們的使命感。”
1981年7月,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曾偕家人重走了一段長征路,並給《生活》雜誌發表了《一個美國家庭重走長征路》一文。重走長征路使布熱津斯基更深入地了解中國特別是當代中國的一些歷史事件。布熱津斯基對長征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長征及其精神遺産為塑造非凡的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剛剛嶄露頭角的新中國來説,長征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部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它是克服落後東西的必要因素——國家統一精神的提示。”
80年的滄海桑田,紅軍走過的山山水水依然在春夏秋冬的交替之中,也許已改變了容顏,但歷史不會改變,人們不會忘記,長征較之公元前400年希臘人從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偉的壯舉”。在世界軍事史專家格裏菲斯看來,中國紅軍“能夠忍耐難以言狀的艱難困苦;能夠戰勝途中大自然好像決意要阻撓他們前進而向他們提出的一切挑戰;能夠擊敗下定決心要消滅他們的敵人而達到自己的目的”。英雄的紅軍用鮮血和汗水繪成了20世紀中國最悲壯的畫卷,在今天、在未來,它仍會吸引全世界的人們去思考、鼓舞他們去奮鬥。 (作者單位:中國延安幹部學院 薛 琳 王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