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視網|視頻|網站地圖 |
| 客服設為首頁 |
莫言,這個名字在10月11日被記在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花名冊上。由他的作品《紅高粱》改編的電影曾打開了讓世界認識中國的一扇窗,而今,帶着他鄉土的根基,他再次為世界通過文學了解中國提供了另一扇窗。 [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
第357期

正如翻譯家林少華在得知莫言獲得諾獎時所言,“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始審美就是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對超越現實、靈魂層面的追求和探討是諾貝爾文學獎的一貫傾向。”往往是追求超越民族、國家,探討普遍的人性和普世價值的比較多,這也是村上春樹等世界一流作家作品的共同之處。而中國人講究入世,文學大多貼近現實、關注社會而莫言則邁出了這一步。
正如諾獎頒獎詞所評價的:莫言“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從他的長篇小説《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可知,莫言的狂歡性想象力與時空遼闊、體量巨大的怪誕歷史敘事暗相匹配。此處“歷史”絕非事實性和公共性的時間概念,而是一個賦予怪誕的過去時想象以合理性和赦免權的空間。
而在其新近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蛙》中,更具這種代表性。台灣版《蛙》的序言裏,有這麼一句話: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在《蛙》的寫作過程中,莫言的心態也與以往不同。因為在他看來,《蛙》是一部冷靜的小説,是一部關於靈魂的小説。我們過去都把目光放在別人身上,拿放大鏡尋找別人的罪過,很少有人認識到自己的罪過。“人只要認識到靈魂深處的陰暗面,才能達到對別人的寬容。作為作家,應該對他人抱有同情。哪怕他是十惡不赦的惡棍,那怕他無中生有地造我的謠言,那怕他將唾沫啐到我的臉上。因為他本來可以成為好人的,成為惡棍,是他的最大不幸。如果能達到這一高度,才是真正的寬容,才能達到真正的悲憫。”
陳曉明在評價莫言時這樣説,莫言的小説可以找到當代國際學界最熱門的所有的主題,既是現代性的表達,又充滿後現代的蠱惑人心的意味。20年過去了,莫言的寫作依然旺盛,筆力狂放,就説是隨心所欲,我行我素也不為過。那些語詞、情感、戲謔、快樂,就象他家鄉的紅高粱一樣,始終那麼茂盛!多年來,我們一直困擾於中國本土的漢語寫作如何與世界接軌,如何是與世界一流大師的作品比肩,中間橫亙着一道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門檻,就把本土寫作擋在現實主義的藩籬之內憋死。

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文壇上興起了一股“文化尋根”的熱潮,1985年韓少功率先在一篇綱領性的論文《文學的“根”》中聲明:“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應該“在立足現實的同時又對現實世界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迷。”
莫言的創作與尋根文學的特徵十分切合。對生命力的掙扎頌揚與對文化的批判提升了尋根的內在要求——從追求自然的根到追求精神的根。學者鄧曉芒認為,“真正的精神的尋根,需要智,需要勇。需要反思的心力……莫言看穿了這種尋根意向的虛偽,展示了它戀母、戀乳和厭食的本質,唾棄了它的愚昧和怯懦。”
《豐乳肥臀》把故事的背景置於遍地英雄的抗日時期。幾家勢力戰的昏天黑地;人性、正義、是非,都被淹沒在海洋一般的仇恨中。但與類似作品風格迥異的是《豐乳肥臀 》並不着意刻劃民族氣節的英雄與悲壯,而是集中描寫上官氏一家人的顛沛流離、支離破碎。
有評論稱,其作品在最原始的層面:食色——人的天性和基本的生存慾望,提煉出生命力的主題,把生命的物質形態發揚到極致。而傳統文化中的積弊對人性、獨立個性的壓抑必然導致內在生命機制的反抗。
恰如莫言自己説過的那樣:“這時我是強烈地感受到,20年農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難,都是上帝對我的恩賜,雖然我身處鬧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鄉,我的靈魂寄託在故鄉的回憶裏,失去的時間突然又以充滿聲色的形式,出現在我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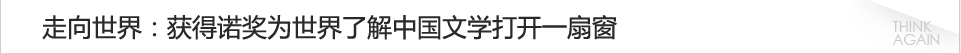
莫言文學的鄉土尋根特質賦予了他特別的本土性,而這種本土性同時也是世界了解其作品的興趣點所在。而這次莫言的獲獎,無疑又進一步推動了這種中西文化的交流。
北京師範大學張清華教授在德國講學期間,曾問過包括德國人在內的許多西方學者,他們最喜歡的中國作家是誰?回答最多的是余華和莫言。問他們為什麼喜歡這兩位?回答是,因為余華與他們西方人的經驗“最接近”,而莫言的小説則最富有“中國文化的色彩”。因此張清華認為:“很顯然,無論在任何時代,文學的‘國際化’特質與世界性意義的獲得,是靠了兩種不同的途徑:一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種族和地域限制的“人類性”共同價值的含量;二是其包含的民族文化與本土經驗的多少。共通的部分讓西方讀者容易感受和接受,獨異的本土氣質又散發出迷人的異域特色,吸引着他們的閱讀興趣。而莫言顯然在本土經驗和民族文化方面有着更為突出的表現。
在這一點上,莫言的自我評述是:“自己的小説引起較多翻譯家的關注和西方出版者、讀者的興趣,還是因為我的小説有個性,思想的個性,人物的個性,語言的個性,這些個性使我的小説中國特色濃厚。我小説中的人物確實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起來的。我不了解很多種人,但我了解農民。就像法國的建築大師保羅•安德魯之所以對我的小説感興趣,就是因為我的小説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原因。” 莫言認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進西方讀者,不是政治原因或其它原因,最終是靠文學作品的自身力量。要看作家是否寫出人類普遍的境遇,是否寫出了打動了所有國家、所有人的情感。
評價莫言很難。卡夫卡説:“藝術是一面像表一樣‘快走’的鏡子。”作家,當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