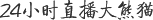原標題:
央視網消息(記者 王甲鑄)2002年春天,一個承諾徹底改變了張應龍的人生:放棄年薪20萬的外企工作和房地産生意,在毛烏素沙漠腹地承包了一塊42.8萬畝的荒沙,至今的17年裏,他再也沒有離開。
17年時間,張應龍所把所承包荒沙的植被覆蓋率由最初的3%提高到70%,完成治沙管護輻射面積達到約50萬畝,栽植各種樹木2500萬株。他本人在2015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是陜西榆林第三代科學治沙的模範人物。
張應龍説,這17年來,與其説是自己改變了沙漠,不如説是沙漠改變了自己。

張應龍在自己承包的荒沙地裏。(記者 王甲鑄 攝)
一個承諾開始漫漫治沙路
故事發生在陜西神木,張應龍的老家。90年代他選擇離家到北京闖蕩,曾是一家外企副總,年薪高達20多萬元。2002年春天,在和老家朋友們的飯局上,醉酒的他説要帶著資金回來治理沙漠。兩天后有人打來電話:“你説要回來治沙,説過的話算不算數?”張應龍是個信守承諾的人,説過的話無法收回,於是,他確認要把那番關於治沙的“豪言壯語”做為人生的一個鄭重承諾,也從此戲劇性地走上了治沙之路。
當年,他以個人名義承包了神木市禿尾河源頭42.8萬畝荒沙,開始了漫漫治沙路。
治沙之難,遠遠超出張應龍的想象,荒涼又凶險的毛烏素沙漠一開始就給了張應龍一個下馬威。
當他第一次去看承包的沙地時,才發現那裏幾乎沒有道路,小轎車根本就開不進去。第二天他又借了一輛越野車,從溝口到準備造林的地方不到20公里路程,走了近6個小時。頭一年幾乎花光了幾百萬積蓄,還被迫賣掉了神木縣城的房産,最窘迫時,口袋裏只剩下不到50塊錢,家人們一度認為他精神上出了問題。
張應龍説:“治沙是好事,但不是我思想境界高,我是逼上梁山的,吹牛吹出去了,沒有辦法,無數次想退卻,但無數次又堅持了下來。”他無法接受自己狼狽的失敗。
治沙與科研“良性互動”
張應龍當過教師、縣誌編輯,在外企當過高管,也曾出國去往德國和日本,這些經歷讓他有著與石光銀和牛玉琴等老一輩治沙模範截然不同的治沙邏輯。
2003年,他開始調整自己的治沙思路,首先發起成立了神木縣生態保護建設協會,希望通過協會公益性的號召動員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進來。先後與中科院地理所、中國林科院、中國農科院以及國外的科研機構等陸續展開闔作,圍繞毛烏素沙地綜合治理等課題,在他所承包的荒沙區進行開發研究。

長柄扁桃經濟林區科學監測設備。(記者 王甲鑄 攝)
終於,治沙與科研的相互作用産生了顯著的“良性互動”。17年來,根據承包區沙地現狀,張應龍探索出了混交林、生態林經濟林兼顧、喬灌結合等模式,在近50萬畝荒沙裏人工造林38萬畝,這讓圪醜溝荒沙區的生態條件得到根本性改觀。在這裡開展的相關課題也取得了20多項研究成果,其中有8項獲得國家發明專利,一大批中省市和國際性的科研項目相繼落戶。
也因此,在榆林眾多的治沙勞模中,張應龍雖然參與治沙的時間最晚,但治沙面積最大、方法更科學、效果更突出。
他的治沙方法到底有多科學?在圪醜溝長柄扁桃經濟林區,記者看到,沙地的水分、土壤、風速都處在實時監測當中,監測數據也實時傳送給相關的科研單位。“我説了不算,一切都要聽科研人員的。”張應龍説。
治沙17年 人被沙漠改變

從神木市區往西,車行一個半小時就來到了圪醜溝。臨近沙區,沙漠深處滲出來的清泉匯集成潺潺溪水,緩緩流淌。站在烽火臺上,昔日無邊無際的荒沙已經完全被植被所覆蓋,數萬畝常樟子松林地在四月中旬的塞北綠意蔥蔥。
面對記者,張應龍頭頭是道:“老是説治沙造林,其實所有沙害是風造成的,治沙主要是要把風防住”“我們不是春天造林,是隨雨造林,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樹和人一樣,吃不飽就會免疫力降低”“人總是站在人的角度考慮問題,而很少站在沙漠的角度上考慮”“每一棵樹都有生命,都有存活的意義,樹也在按它的方式在思考……”

用張應龍自己的話説,他希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傳機會,宣傳自己的生態文化理念,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通過植樹造林,重視生態保護。
站在樟子松林地裏,張應龍感慨,過往的17年是他不斷學習的17年,和大自然學習,和沙漠學習,和科學家們學習。“不是我改變了沙漠,是沙漠改變了我,這片地方,如果你熱愛它,它就是世外桃源。如果不熱愛,它就是地獄,我曾經40多天在這裡沒和外人説過話,那種孤獨無法描述。”
張應龍説,沙漠裏不會説話的樹把會説話的他忽悠了這麼多年。“它每年長一點,每年長一點,總讓你有希望,讓你不斷付出感情,就這樣一直‘勾引’著你堅持到現在。有時候面對子女,會很愧疚,但是只要站在這片沙地裏,一切就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