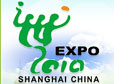1946年逝世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上周辭世的米爾頓�弗裏德曼,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由於弗裏德曼曾花費大量精力抨擊凱恩斯留下來的學説,人們自然會認為他們是相互對立的。的確,他們之間存在深刻的差別,但兩者的共同之處亦是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他們都不是贏家,也不是輸家:今天的正統經濟政策,是兩人學説的綜合體。
凱恩斯從“大蕭條”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自由市場已宣告失敗;弗裏德曼則認定:失敗的是美聯儲。凱恩斯相信像他自己那樣思想深邃的政府官員的判斷力;而弗裏德曼認為,只有受到嚴格規範制約的政府才是“安全”的。凱恩斯認為,需要對資本主義加以束縛;而弗裏德曼則認為,若放開手腳,資本主義將呈現恰當行為。
這些差異不言自明。但雙方的相似之處同樣明顯。兩人都是才華橫溢的記者、辯論家和自身觀點的倡導者。兩人都認為,從根本上講,大蕭條是一場總需求不足導致的危機;他們都撰文支持浮動匯率,支持名義(或法定)貨幣;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重大鬥爭中,兩人都站在自由的一邊。
但凱恩斯雖然從氣質上講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也是一個江河日下的國家裏,中上階層的悲觀一員:他認為,要保留相當程度的自由,就要放棄19世紀正統理念的許多要素。而弗裏德曼作為貧窮的猶太移民之子和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較為樂觀:他希望重振自由市場,並對政府進行限制。
為實現這一目標,弗裏德曼試圖推翻在他看來凱恩斯及其繼承者所犯下的錯誤:從當前收入進行消費的固定傾向推動總需求這一假設;認為財政政策是最有力的政策工具這一想法;相信名義需求的變化將導致實際産出的持續變化;對政府運用其判斷力抱有信心等。
備受爭議的弗裏德曼論
上世紀60年代,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弗裏德曼對自由市場的信奉以及對凱恩斯理念的反對是邪惡、誤入歧途的,甚至兩者兼而有之。70年代的大幅通貨膨脹──和平時期的空前水平改變了輿論氣候。1971年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並轉向浮動匯率體系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這一轉變發生在價格飆升之前。
在這個匯率或多或少地自由浮動,而通脹急劇上升的世界,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提供指引。當時人們寄希望於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以貨幣供應為指標。美聯儲前任主席保羅�沃爾克于1979年至1982年在美國嘗試了這種做法。瑪格利特�撒切爾當政時的英國政府也于1979年至80年代中期,進行了此種嘗試。在這兩次嘗試中,通脹都被摧毀,但貨幣與名義需求之間的關係也隨之崩潰。凱恩斯理論的確已經死亡。但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主導地位也同樣逝去。
受規則約束的決策機制
其後,一種新正統學説從廢墟中興起:正如弗裏德曼所言,經濟政策應瞄準一個名義變量目標,而非實際變量目標;目標應當是通脹這一目的,而非貨幣這一手段;為了實現目標,各國央行應根據需要自由地調控利率。這就成了一種受規則約束的機斷決策機制。弗裏德曼贊成遵循規則;而凱恩斯贊成機斷決策。弗裏德曼勝在將貨幣政策置於首位;而凱恩斯勝在拒絕接受數量理論。
但從最重要的意義上講,兩人都獲得了勝利。過去20年間,名義貨幣主導的世界做到了通脹水平適度,併為經濟穩定增長提供了支撐。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弗裏德曼本人今年初曾表示:“艾倫�格林斯潘的偉大成就在於,他證明了維持物價穩定的可能性。”這是一位偉大的規則倡議者,對一位偉大的機斷決策運用者的讚譽。
以通脹為目標的獨立的央行和自由浮動的貨幣,是不是宏觀經濟政策的“歷史終結”呢?筆者覺得不是。浮動匯率的反復無常,似乎在呼喚另一次貨幣一體化實驗,甚至嘗試一種全球化的貨幣。
科技進步甚至可能使貨幣變得多餘,使其僅限于發揮記賬單位的作用。
政策辯論也將繼續。歐洲央行或許終將説服它的同行,讓它們相信貨幣數據給人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同樣,各國央行或許也會認識到,它們忽視資産價格的行為存在風險。甚至可能還會再度出現對擴張型財政政策的需求,正如上世紀90年代日本通縮時期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
同樣不確定的還有市場經濟的未來。兩人目前在這方面打成平手。凱恩斯可能會擔心,放開資本流動可能産生影響經濟穩定的後果。而弗裏德曼則不得不承認,全面縮減政府角色,並不在議程上。市場的確已經擺脫了20世紀中期的許多桎梏。但政府控制著資源,調控著經濟,其程度在一個世紀前是無法想象的。全球化本身也可能失敗。
凱恩斯和弗裏德曼是上世紀那場政策辯論的主角。但我們今天看到,他們既不是贏家,也不是輸家。
《國際金融報》 (2006-11-28 第04版)
責編:韓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