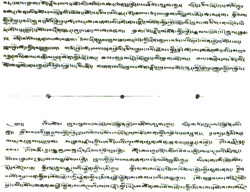
原西藏“噶廈”(地方政府)制訂的《十三法典》部分條款。
要認識過去的西藏社會,就必須了解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對於我們這輩人來説,要認識西藏政教合一政權下的農奴制,唯一的途徑就是書籍了。當然,我在七十年代中葉至八十年代中葉在西藏當教師時,也曾有機會去過江孜的一處大莊園帕拉莊園。但是從一座空空如也的莊園裏很難得到切身的感受,因為,現在的許多農民的住家已超過那座莊園的規模了。可是一些為數不多的書籍,那些親歷者栩栩如生的描寫,讓人看了一次,就再也不會忘記。在這裡,我們摘錄一些他們的話。因為這會比我的敘述更令人信服。

舊社會的監獄(拉薩“朗子轄”)裏用作銬“犯人”的木腳鐐。這種刑具,每副能銬四、五個人。
法國藏學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中説,舊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他們身上還有著苛捐雜稅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

不堪重負——拉薩市郊的女農奴們在背負麥草回村
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揭桓鲆丫骨辶蘇竦娜恕庋煥矗信┟窬妥勻歡壞匾艿礁呃吶貪K遣壞貌幌虻胤繳係暮狼咳繾詒盡⒛澄渙熘韉墓薌乙約案澆略旱淖芄芙棖⒔枇浮⒔梟螅舛家ジ逗芨叩睦ⅲセ溝鬧遼僖仁導式璧降母叱鲆槐叮綣墻棖扛鱸鹿飫⒕褪前俜種?

農奴必須定期無償地為領主勞役。在農忙季節,甚至放棄自己的農田,首先要去領主的地裏勞動。這是一張化工單。一個農奴勞動一天,換來的僅是管家一枚圖章印記而已。
難道用來年的收成就可以還清高利貸者的債嗎?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還不起債,還得請求債主們讓他們繼續借下去,或者續借未還清的那一部分。由於拖延償還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寬限,僅有的糧食以及保存下來的其它食物,幾乎從來也不夠全家吃到來年收穫時節。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他們只好再借,藉口糧,借種籽……如此下去,年復一年,永無完結,直到臨死的時候也不能從債務中解脫出來。而這些債務就落到了他兒子的身上,可憐的兒子從剛一開始種田生涯起,就受到這些祖傳的債務的壓榨,而這些債的起源早已是遙遠的過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這從什麼時候説起。

山南凱松莊園的農奴和奴隸們在服勞役——為領主索康�旺清格勒捻毛錢。
除了直接的債務外,藏民們還有捐稅方面的負擔。

在西藏金龍谿卡,一個年已八十余歲的老農奴在為農奴主服勞役——製作酥油。
我旅行時身上穿的是藏袍,開口講的是藏語……因此他們很直率地同我説話,毫無隱瞞地向我訴説著他們的痛苦與窮困,以及壓在他們身上的苛捐雜稅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還常常迫使他們在農忙時節離開田野,這些無償的義務,實際與一切壓在藏族人頭上的其他重負並無區別。到處都在為官府施工,修築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門。所有這些繁重的勞役都壓在可憐的村民身上,他們既無工資,也得不到飯食。而除了官府強制分派的工作外,農民們還得無償地為那些手持差票的過往客人運送行李和貨物,還必須為他們及其隨從提供牲畜,飼料和食糧。……像所有他們的同類人一樣,這些農民都是可憐的農奴,他們沒有權利也根本不可能離開家鄉,去尋找另外的土地和不過分苛刻的頭人。他們中間有幾個人也曾經逃到鄰近的地區去,但最後還是被頭人從新家搶出來,帶回村子,吃了一頓棍棒被判罰鉅額罰金。由於非常懼怕頭人對其親屬施行的懲罰,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為一人逃走,所有親屬就得遭殃。頭人會譴責他們沒有阻攔出逃者,那麼,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親等人就會被頭人抽打一頓,然後再替他償付罰金。

朗吉,在舊西藏是是一個貧苦農奴,由於交不起農奴主的稅金,競被砍去左臂。
西藏的民歌這樣唱:“山上有沒有主的野獸,山下沒有沒有主的人。”為什麼農牧奴不能離開土地?現代人類學家梅爾文�C�戈爾茨坦、辛西婭�M�比爾通過實地研究,在他們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國人眼中的西藏》指出:“西藏的制度通過把勞動力配置在這些領地上使領主大獲其便”。

與野狗爭食的西藏兒童。
“拉格雅帕�伊荷強的牧民家庭擁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願進行管理和處置。但是他們不能隨便離開這片土地,或帶著牲畜到另一個領地去,即使那裏歡迎他們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強實行的這種封建式‘領地’制度在西藏的農業區也並行不悖,它確保了宗教界和貴族上?閎宋錚ㄒ約罷舊恚┯滌幸歡ǖ睦投純七撬刂頻耐戀亍4穎局噬纖擔械耐戀囟際粲誒奈韃卣羌赴倌昀矗薊楣笞寮易濉四蠡罘鵂八旅硭校源俗魑湫奚煞押臀稚頻睦叢礎S捎詮庥型戀兀揮欣投錘骰蚍拍粒還蓯橋┮蹈鼗故悄燎蕕兀疾荒艸晌鈄柿希虼宋韃氐鬧貧韌徂牙投ε涫粼謖廡┝斕厴鮮沽熘鞔蠡衿潯恪4穎局噬峽矗枇熘韉牧斕賾脛惺蘭團分蕖伍扯硨頭飩ㄈ氈臼貝牟梢胤淺O嗨啤!?

西藏農奴主索康�旺清格勒的一個奴隸次仁卓瑪,由於年老力衰,被放逐出家園,只好靠行乞為生。這間廁所,成了她棲身之地。
大衛�麥克唐納在他的《西藏寫真》裏寫道,“西藏最嚴重的刑罰為死刑,而喇嘛復造靈魂不能轉生之臆説,於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體開顱之慘狀。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將犯人縫于皮袋之內,而擲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約5分鐘開始下降,後視其猶有生息,則再擲沉之,迨其已死,於是將其屍體,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軀體投之河中,隨流而去……。斷肢刑,用於冒犯及抗拒之確有證據者,而小賊在曠野搶劫,亦用此刑。斷肢刑係將其手與足切斷,四肢當切斷時,務須縛緊,以免血跡之溢流……斷肢之外,又有一種剜眼之兇刑,或用凹形之煨鐵,置於眼內,或用滾油,或開水,倒于眼內,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視力,然後將其眼球用鐵鉤攫出……囚犯一人監獄,罕有能避免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種種摧殘,而損失喪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濕、黑暗、污穢及有害於衛生之土牢中,永遠不見天日。西藏官府,對於罪犯,每日只發些微之口糧不足維持其生活……。且西藏之罪犯,又間有鞭害及痛拷之刑。又制一種絞鏈,以鎖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開釋之,以復其自由。有時亦用枷刑,配以鐵鎖。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實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兩手分開,面孔貼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攜皮鞭或柳條,以笞撻其大腿之兩臀……
《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裏寫道,西藏的刑法是嚴厲的。除了罰款和監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審判過程中,受到鞭打的不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還有被告甚至見證人。對嚴重違法者,既使用頸枷也使用手銬。頸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塊沉重的方木塊。對殺人犯和慣偷慣盜,則使用鐵制腳鐐。對很嚴重的罪,諸如謀殺、暴力搶劫、慣偷或嚴重的偽造罪等,則要剁手(齊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於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謀殺罪的人被裝進皮口袋,縫起來,給扔進河裏。

西藏民主改革前拉薩的一個貧困區——魯固幫倉。
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個地區的首腦,即宗本,還有莊園主(當案件只涉及他們的佃戶時)。另有四名地方長官負責處理聖城及其近郊的案件。這些地區行政長官中,有一名可以隨意鞭打被告人,高興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興幾時打就幾時打,只要不將其打死就成。當被盜財産尚未找回之時,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幾次,以誘使他説出被盜財産藏在什麼地方。宗本所科罰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將小部分提交政府外,其餘大部分歸他本人。
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聖地西藏》裏説,“偷竊所受到的懲處最為殘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樣,犯這種罪的人多為居民中的窮人。在拉薩,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貪圖別人的財産而受到了懲罰的人,他們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從事乞討的盲人。其次,西藏還習慣於讓罪犯終生脖套圓形小木枷,腳戴鐐銬,流放到邊遠地區和送給貴族或各宗長官為奴。”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薩真面目》説,西藏沒有強大的中産階級。控制著封建領主的是僧侶。因為西藏人虔信他們那種形式的佛教,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沒有僧侶也無能為力。這個“國家”(引號為引者所加)實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農民是他們的奴隸。……這些窮人和那些小佃農毫無怨言地為他們的精神上的主人幹活,對這些人他們懷有盲目的崇拜。雖然他們要將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強的那部分交給寺院,但他們並沒有不滿情緒。必須記住的是,每家每戶至少要送一人去當喇嘛。

從尼木流浪到拉薩的逃亡農奴,舉家露宿街頭。
這些內容,顯而易見都是當時筆者親眼所見,從這些為數不多的實錄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封建農奴制的黑暗和殘酷。假如真如現在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所説,過去的制度中的社會是一種最好的理想社會,那麼看了以上幾段文字後,人們該知道舊西藏的“佛光”是如何“照耀”廣大農奴的,這種農奴制度又是如何“以佛教為基礎,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了。(張曉明)
責編: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