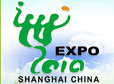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7年01月08日 14:57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 記者馬曉華發自北京
這是一項“中國之最”:一位老人在哈爾濱某醫院住院66天,住院費用139.7萬元,平均每天2萬多元。而病人家屬又在醫生建議下,自己花錢買了400多萬元的藥品交給醫院,作為搶救急用,合計耗資達550萬元。
但幾百萬元的花費沒能挽回老人的生命。今年8月6日,老人因搶救無效在醫院病逝。
這位花費了鉅額醫療費用的老人名叫翁文輝,生前是哈爾濱市一所中學的離休教師。一年前,74歲的翁文輝被診斷患上了惡性淋巴瘤。因為化療引起多臟器功能衰竭,今年6月1日,他被送進了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下稱“二附院”)的心外科重症監護室。
出於對鉅額費用的不解,患者家屬先後寫了100多封舉報信投遞給相關部門。11月下旬,中紀委、中紀委駐衛生部紀檢組、監察部駐衛生部監察局聯手組成調查組,赴哈爾濱對此事進行調查。
“二附院被調查的人員今晚離開北京,現在中紀委調查組的人已把核實過的相關資料拿走了。”患者翁文輝的長子翁強昨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為了父親的生命,錢,似乎不是最為重要的事情,但是67天花費500多萬元,卻讓翁強感到納悶。
“66天共有3025份化驗單,我手中有一疊的調查報告,但是其中只有35份是合格的。”翁強氣憤地説,“7月25日和8月1日,這兩天每天的輸液量將近一噸,7月25日輸了 78604ml,合1572.08 斤,8 月1 日輸了69307ml,合1386.14 斤,如果是正常的人,輸液也能輸死,更何況一個病人,誰的心功能有這樣好?”
二附院一位醫生對此表示,從血液治療的角度看,無法判斷這些輸液量是否超量。
翁強還告訴記者,他父親住院期間,“66天做了588次血糖分析,299次腎功能檢查,平均每天4.5次,而且每天都乘4,我不知道這個4倍是什麼意思?66天做了血氣分析379次,化驗血糖輸液1692次,輸血968次……”
記者在翁文輝的“住院病人費用明細單”上發現,惡性淋巴瘤病症禁用藥物“尊怡”每天都有使用記錄。
“最讓我弄不明白的是我父親在8月6日去世,但是8月8日還在做痰培養的檢驗。”翁強表示,“我父親住院66天,醫院收了88天的錢,而且到了8月15日結賬時,預交款剩餘的8萬元成了零。”
對於患者家屬強烈質疑藥費和化驗費,二附院調查組于9月下旬向患者家屬遞交了一份初步調查報告。調查報告顯示,在用藥方面,醫院不是多收了就是漏收了,沒有一份收費單據合格;化驗方面,收費單比報告單多出128次,2119份病房化驗報告單中,合格的只有35份。
公安部介入調查醫院賬戶被封
本報記者馬曉華發自北京
哈爾濱“550萬天價醫藥費”事件又有新進展,公安部日前已介入調查。
公安部專案組一位官員昨日在答覆《第一財經日報》的諮詢時表示:“只要是涉及到案件的責任時,公安部就會介入。”
死者家屬告訴記者,此次調查涉及到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下稱“二附院”)的院長、診療小組人員以及死者家屬,目前專案組有關人員已經與死者家屬接觸,並取走了一批資料。
二附院一位內部人士告訴記者:“現在醫院的賬戶已經封了,職工的工資、獎金都發不出來。來醫院看病的患者也特別少。”
5張病歷6種字體
“這件事我真的不想再説了,畢竟我的父親已經去世了,每説一次,我都會痛苦一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死者家屬仍沉浸在悲痛中。他對記者表示,看到醫院、醫生,這個讓每個人都敬重的地方和人,卻是如此對待病人,他非常氣憤,“我不想讓其他人再受到這樣的欺詐。”
死者家屬給記者出示了一個箱子,裏面盛滿了各種單據:“這些都是證據。但是有些東西還不全,比如病歷,我們只有5天的。這還是要過來的,其他61天的記錄都沒有。”
死者家屬告訴記者,他們幾經週折,才從醫院要到了從6月1日到6月5日的病歷記錄。在僅有的5天記錄上,卻發現諸多偽造的痕跡。
“從時間到字跡到內容,都是接不上的。”死者家屬説,“病歷上連治療方案都沒有,不知道是怎麼監護的。”
病歷為規範的文案,是病人治療和搶救的佐證,不允許有任何塗改、偽造,必須保證病歷和治療過程的完整、及時、準確。而記者卻在這5張病歷上看到6種字體。
死者家屬表示,連王雪原醫生(翁文輝的主治醫生)本人也證實了這些病歷非其本人簽名所開,王雪原對此也不知情。
賬單之誤
死者家屬還給記者出示了兩份收費單,一份是交費時的白單,一份是結賬時的藍單。但在這兩份單子上,就憑空多出許多沒有項目的費用,即使同一天的收費單,白單和藍單都是不同的數字金額:
2005年7月25日,收費單經核算顯示輸入液體43464ml,而特護記錄單實際顯示輸入液量5925ml;
2005年7月30日,收費單經核算顯示輸入液體40092ml,而特護記錄單實際顯示輸入液量11075ml;
2005年6月7日,收費單顯示查血氣分析28次,而特護記錄單實際顯示僅有14次……
另據介紹,死者在二附院重症監護室(ICU)住院期間,死者家屬根據ICU主任的通知,在66天內從國內外共計買回藥品價值達400多萬元,每次將藥品都交于ICU主任和其他指定醫護人員,大部分藥品ICU都出具了手續。
死者家屬提供的交給ICU的部分藥品清單顯示:2005年6月13日,醫囑上寫著66支沐舒坦,實際領走了132支,其中66支不知去向;6月9日,醫囑寫74支,實際領走90支,16支不見了。也就是説,在這兩天裏,二附院給病人用了140支沐舒坦治療,實際卻領走了 212 支。
另外,在6月3日,二附院給病人使用白蛋白5支,卻收了10支的費用;萬古黴素醫囑使用2支,收取了4支的費用;日達仙用3個,卻收取了10個的金額。
聯合調查組全方位調查“天價醫藥費”事件
本報記者馬曉華發自北京
中紀委、中紀委駐衛生部紀檢組、監察部駐衛生部監察局聯手組成的調查組,對哈爾濱“550萬天價醫藥費”事件的調查,正在不斷深入並向全方位展開,從患者家屬、醫院直到衛生廳。
與這一全方位調查相呼應的,是廣大群眾和醫療工作者對醫院和醫療系統服務患者的系統性反思。
本報接到北京市的一位患者家屬的電話:“我的夫人先是在北京某醫院住院,由於病情的需要,轉院了。明明是當天下午5點轉的院,但是吸氧卻吸到第二天的上午10點。雖然錢不多,但是這樣的行為如果每天每個病人身上都會發生,這筆賬卻是可觀的。”
但從事醫療衛生行業的人士似乎也有著自己的苦惱。“誰又來為醫生説話?無論醫生、護士、患者,還是政府官員都在要求醫療制度改革。但是,實際上卻是不成功的。”一位醫生直言不諱地在網絡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這位醫生接著寫道:“如果你來哈爾濱醫科大學二院看看,你就知道這裡的設備和條件是多麼的好;同樣,這些年來(醫院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們也承認,醫院應該有著它自己的本來面目,即具有福利性質。但福利性質是要有堅強的國家支持為後盾的。可以這樣説,現在醫院最先進的移植技術就是幾代醫護人員堅持不懈的努力所換來的。”
“難道人不應該體現自己的價值嗎?每天外科醫生要站在手術臺上幾個或者十幾個小時,就連回家吃飯都要提心吊膽;晚年,會有腰間盤突出、頸椎病、心臟病、腦血管疾病。但價值體現呢?醫生護士的基本工資僅僅是1000元/月左右!”這位醫生明顯是感觸良多,“你相信一個救死扶傷、一個在刀尖上舞蹈的人經濟價值就這樣可憐嗎?如果沒有獎金及紅包的收入,又能吃什麼?我相信現在就連一般的工人都可以賺到1000元/月的工資而他們不用讀專業6年以上,不用每天精神高度緊張。”
但相比之下,患者的怨言更多。一封患者家屬來信反映,唐山市豐潤區西歡坨村的患者吳某某,2005年8月30日在唐山某醫院就醫,因為誤診耽誤了治療時機而死亡,患者家屬最後才知道,不但管床人員沒有註冊職業醫師證書,而且全部參與治療的護士均無註冊證書,一起無證行醫的事故就發生了。
而另一封來信則反映,發生在北京某女子醫院的子宮消融術,子宮肌瘤沒有被消除,腸子卻腐爛了,最後把結腸切除了7厘米,但是當病人去醫院要病例報告的時候,卻被告知已經沒有了。
CBN 記者對話CCTV 記者
“我們在和一個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體較量”
本報記者馬曉華發自北京
正當醫改方向的討論席捲全國之際,黑龍江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550萬元醫療費事件”,無疑又給人們沉痛反思醫療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契機。《第一財經日報》日前對話最早揭開此番醫療“盤剝”的央視新聞調查記者
郭宇寬,感受其不為人知的艱難。
長達9天的實地調查
《第一財經日報》:作為“天價醫療費”的電視第一報道者,您當時的反應是什麼?
郭宇寬:哈醫大二院在業界非常有名,其心外科更是聲譽顯赫,當我們接到投入500多萬元卻把老爺子給“治死”的舉報時,第一個反應就是“有沒有搞錯!”加上家屬的情緒非常激動,大家都懷疑這則舉報的真實性。直到有一天家屬傳來了部分收費清單的複印件,我們才感覺到問題的嚴重。為了避免帶著簡單的義憤作“缺席審判”,記者在哈爾濱進行了長達9天的實地調查。
《第一財經日報》:您首先採訪的就是心外科ICU(重症監護室)科室主任于玲范?
郭宇寬:心外科ICU科室主任于玲范是患者家屬控訴的焦點,黑龍江當地媒體曾高調宣傳過此人。一開始記者只是扮做看望朋友在醫院裏暗訪了一圈,見到的情景頗為混亂:不時有醫托搭訕,有收藥的,甚至有上訪的,還有人在大堂見人就拜,求求誰能和醫院説説好話,因為帶的錢不夠。在確認了心外ICU科室位置,並確認主任于玲范就在辦公室以後,記者和攝製組敲門進去,自報家門,進行突擊採訪。
于玲范當時正在改一篇和別人聯合署名的醫學論文,桌上還有一摞某消費場所的贈券。一提翁文輝的名字她就緊張起來,對於記者的所有提問,她基本上反復用三種方式循環回答:第一,對於治療不懂,醫囑都是北京請來的專家下的,我們只是執行;第二,這個情況太具體,我作為主任不管,你得問護士;第三,醫院已經成立專門調查組進行調查,你可以問調查組。
《第一財經日報》:後來院方出面了沒有?
郭宇寬:醫院紀檢委書記楊慧之後作為調查組組長接受了採訪,但是她的態度更加強硬,她先是質疑記者的資格:“你們對醫療問題了解多少?”“你們受什麼人的指使?”“我們這是一家為貧下中農服務的醫院……”在記者的追問下,她鄭重説出了院方調查組給這次醫患糾紛的定性,第一,對於這位患者,在收費問題上,非但沒有多收,而且經過核對少收了很多;第二,如果在收費中有錯誤,那是因為對這個病人“過於照顧”,所以破壞了管理制度,造成了混亂。而其他醫療方面的問題,她都解釋不了。
《第一財經日報》:從他們的反應判斷,這家醫院似乎在“天價醫療”事件上有著不為人知的故事。否則,他們為何刻意回避。
郭宇寬:在採訪中我們挖掘出了一些院方自相矛盾的解釋地方,比如于玲范解釋之所以有時候一天在賬單上用血量達到一萬多毫升,是因為血庫用血緊張,所以經常一次取出幾天的量。而輸血科主任丁巾則一口咬定,絕不可能有這種情況;再比如對於一天之中輸血94次,也就是輸了94袋血製品,護士長郭曉霞最初説完全有可能,但是記者後來詢問她輸一袋血,最快要多長時間,她脫口而出:“以前最快半個小時輸過一袋,再快病人心臟就受不了了。”但她剛説出口就意識到語失,記者追問:“假如24小時都用這種最快的速度,能輸多少血?”她想了想説“沒有算過”。
《第一財經日報》:我們從患者的病例上似乎也看不到治療方案。
郭宇寬:這就是為什麼説跟醫院相比我們是一個弱勢群體的原因。治療方案或者病程記錄,我們都要不出來,找醫院,醫院説都給家屬了。家屬也要不出來。即使後來又帶著攝像機去拍去要,院方也是不給,説記錄都給於主任要走了。
《第一財經日報》:院方之所以這樣對待我們,就是看到我們反正找不到確實的證據。
郭宇寬:是的。院方自信地知道,你的所有懷疑只是一種懷疑,這就涉及到了ICU的特殊性,記者在調查中深感,ICU對於外部監督來説,是一個天然“黑箱”,ICU的功能是集中地使用維持生命的醫療技術,擁有各種措施支持廣泛的器官功能不全。
這就造成了監督的缺失。首先,ICU的病人都喪失了行為和表達能力,喉管被切開,身上插滿管子,手腳被綁在病床上,身上沒有衣服,只蓋床單,聽憑醫護人員的擺布。而病人的家屬又不在身邊,也不能探視,只能聽護士轉達病情。而用藥過程也無法監督,究竟用了多少藥輸了多少血,都只有裏邊的人才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屬説的:“就是他們虐待病人,我們也沒有一點辦法。”
記者曾見到用鉛筆潦草地寫著“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帶我回家”等字條,是患者在護士短暫離開的間隙給家屬留的。可當記者詢問患者家屬,既然對ICU病房的工作人員已經不信任,為什麼不投訴呢?富秀梅哭著説:“我們不敢呀,老伴的喉嚨已經被割開了,離開呼吸機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裏,要是得罪了他們,老頭要受更大的罪呀!我們只有變著法兒討好他們,後來他們全科室吃飯我們家都包了,每天都給他們送飯。”
仍有正直的聲音
《第一財經日報》:我看到你們的電視報道,後來患者的主治醫生終於出來説話了。
郭宇寬:在這樣的調查中你是能明確感覺到你在和一隻看不見的手較量,這是一個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體,整個系統會抱成一團用可怕的沉默和不合作來面對你。
就在這時管床醫生王雪源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他給家屬也留下了比較正直的印象。當記者聯絡到他時,他曾接到過於玲范的電話:“你現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上,説什麼不説什麼,要想清楚。”雖然答應接受記者的採訪,但是可以感覺到他面臨著極大的壓力。最初他和院方一樣含糊其辭,非常緊張,多次停下來喝水。在談到做醫生的原因時,那一刻他眼中閃爍著一種真誠的東西,我能夠感到從那一刻起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作出了選擇,接下來的採訪中,他可以説豁出去了,以一個當事人的身份,無論是輸液輸血劑量,還是外購藥去向,都以親身經歷證實了我們的懷疑。
《第一財經日報》:新聞調查還採訪了一個專家吧?
郭宇寬:結束哈醫大的採訪後,我們雖然有了自己的判斷,但還是得採用專家的意見。我們多方聯絡,卻沒有一個ICU方面的專家願意站出來説話。甚至北京一位參加過翁文輝病情會診並收了30多萬元出診費(翁家兒子翁強事後透露)的某三甲醫院的ICU主任,也不願意評價。
直到聯絡上水利部總醫院前副院長和前ICU主任馬育光,他開玩笑説:“反正我退休了。”他不但從專業的角度解釋了哈醫大二院的收費和管理為什麼不合理,還在賬單中發現了一些新問題,比如ICU儀器的檢測,就是監護儀的檢測,根據規定,北京這個儀器收費是240元一天,可哈醫大二院在收費中把它拆成四項,每項收一遍費用,這樣每天就出來1248元。
在這起醫療事件中,我們發現問題實在太多了,多得連專家都覺得滑稽。用馬育光的説法,一些錯誤太低級了,也太離譜了,可見他們膽大妄為到了何種程度。
我們在醫院面前都是弱者
《第一財經日報》:我回北京見到了患者的兒子。他説的一句話,讓我特別感慨:“我就是想知道一個真相!”其實,他是一個有錢的人,但即使再有錢,在醫院面前似乎也很無奈。這就告訴我們一個事實: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我們其實在醫院面前似乎都是弱者。
郭宇寬:患者大兒子翁強是一個開大奔、住別墅的“大款”,他曾經表態:“只要能治好我爸的病,花多少錢,我都樂意。”確實他調動了各方面的醫療資源,光北京的專家就請了好幾十個去給他爸會診。這讓人感慨,在這個窮人看不起病的年代,一切醫療資源,包括那些被我們尊敬的著名大夫的服務都可以用錢買到。但更讓人感慨的是,患者家屬花了這麼多錢,也買不到一些醫護人員為病人著想的基本職業道德,翁強痛苦地反省:“要不是我有錢,我爸也不會受這個罪了。”《第一財經日報》:不過,讓我欣慰的是,在接下來的採訪過程中,我獲悉中紀委、監察部、衛生部等各個部門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該事件進行調查。可以看出,黨和政府的反應是極其迅速的。而公眾的網上評論更是如潮水般。個人感覺這次事件將對醫療衛生改革起到某種重要的影響作用。
郭宇寬:這個事情感覺有點像醫療界的一個“孫志剛案件”。為什麼這麼講呢?是因為醫療事故在中國不是第一回。而翁文輝事件的奇怪就在於,它是第一次被披露,而且是以一個非常觸目驚心的新聞事實被披露。
比如收容遣送制度,大家都覺得有問題,但是由於不透明,特別是涉及到監獄系統,我們記者無法調查,只能通過知情人透露。對於醫療事件也一樣,大家都知道有問題,比如回扣等,都是大家知道的公開秘密,但是不能像解剖麻雀一樣解剖。但是這次跟“孫志剛案件”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專業性比較強。
天價醫藥費“吹哨人”當面開口
患者翁文輝的主治醫生王雪原表示,事發7月末兩支“克賽思”的離奇丟失
本報記者馬曉華發自北京
作為“天價醫藥費”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患者翁文輝的主治醫生王雪原一直處於風口浪尖。昨日,他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稱,“(當事醫院)在管理上存在很多漏洞,最主要的就是監管缺失。”
事發7月末
按照王雪原的説法,其實在決定説出真相之前,他對醫院早已“有一些想法”。
6月1日這天,王雪原第一次接觸到患者翁文輝。據他介紹,當時患者被診斷為惡性腫瘤,經過化療後多發感染,“從各個系統來講,出現嚴重的代謝性鹼中毒、離子紊亂,低鉀血等”。於是,患者被送到了ICU,因為ICU是提供生命支持的,先是救活,對血液、呼吸等各個系統進行處理。
“因為我是接觸不到費用的,所以一直不知道患者花了多少錢。但是對於過重的治療和過度檢查,我較早就感覺到了。”王雪原説,“這個患者最初的治療強度確實很大,但一直持續這樣高強度的治療是不恰當的。”
王雪原最早確信中間有問題,是在7月末。他回憶,7月末的某天,恰好是他本人值班,值班期間發現患者的自備藥“克賽思”(音譯)沒有了。於是他給患者家屬打電話。患者家屬在電話裏説:“不會啊,應該還有兩支。”
“對於自備藥,患者家屬都知道每天用多少量。但是我去查,確實沒有了。我回憶了一下,應該還有,當時就覺得出了問題,於是提醒了院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但是她沒有在意。”
就是從這時開始,事件一步步放大,直至最終爆發。(相關文章見A2、A3)
監管缺失
王雪原已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下稱“哈醫大二院”)工作了4年。在他看來,哈醫大二院是一家實力非常強的醫院,“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醫院在管理上存在很多漏洞,最主要的就是監管缺失。”
王雪原認為,這種監管缺失主要體現在對醫院高層、主任、護士長的管理權力的監管上。“醫療行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行業,財務制度相當嚴密。但是在哈醫大二院,護士長、主任這樣沒有財務資格的人,卻每天都在進行著會計的工作。”
讓王雪原不可理解的是哈醫大二院對事件的調查。他回憶説:“醫院成立調查組後,我在第一次談話中講了真話。之後,他們就不再找我調查了。我發現,整個調查都是于玲范主任在起主導作用。本應該是被調查對象的人卻成了調查的主導者,這個是有問題的。”
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醫囑上的簽字並非他本人所簽,“只有25%是我簽的。”
“可怕的是出了問題還要掩蓋”
“在決定接受媒體採訪之前,我就有了這樣一個心理準備。經過反復思考,我決定把事實説出來。”王雪原對記者表示。
自從接受媒體採訪後,王雪原説他的同事們對他基本上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支持,而且是非常支持。第二種説他是“漢奸”,是哈醫大二院的“叛徒”。第三種是避之唯恐不及。而關於哈醫大二院的態度,王雪原説:“他們不認同我説出真相的行為。但是我覺得,出現問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了問題還要掩蓋。”
王雪原認為,自己現在所走的每一步都壓力很大。而是否還能繼續從事醫生職業,“取決於自己還想不想”,“如果環境繼續這樣,我就會選擇放棄。”
至於能不能留在哈醫大二院工作,他説“現在還很難回答”。
“我的出發點很簡單,即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希望能儘快給公眾一個完整的真實情況,同時也希望能通過這件事情,來推動我國醫療衛生制度的進步。”王雪原最後説。
翁強自述哈醫大二院問題
本報記者馬曉華發自北京
昨日,就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二院(下稱哈醫大二院)天價醫藥費事件,患者家屬的長子翁強向《第一財經日報》以及其他媒體同時公佈了自己所掌握的證據和材料,並進一步透露了事件的前後經過。
再爆內情
“我依然記得父親生前曾跟我説的一句話,讓我很內疚。他説,‘我本來是哮喘,現在怎麼搞成這樣?’”翁強這樣對記者回憶道。
根據翁強的回憶,在5月21日之前,父親翁文輝的身體的各項檢查都是符合化療要求的,所以就從這一天開始進行了化療。但在化療的過程中,翁強曾提出要求哈醫大二院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把化療藥物中的阿黴素換掉,理由是這個藥的毒副作用比較大。但最終沒能換成。到了5月25日,翁文輝身體的各項指標都在下滑。
5月29日,院方要求翁文輝轉入ICU,但是翁強有所保留。但是ICU主任于玲范表示高幹病房沒有任何的搶救措施,醫院只有ICU有搶救措施。如果不搬入ICU,患者發生哮喘搶救不過來的話,醫生不負責任,要求家屬簽訂協議。於是,翁強買了一台呼吸機。
之後,翁強看到父親的病情稍微有些好轉,於是決定在5月31日下午4點40分回北京。但他剛剛到北京的當日,他就接到了家人的電話,時間是19點09分。電話説自己的父親不行了,於是他又重新返回機場,直奔哈爾濱。當他到達哈爾濱的時候,展現在他眼前的一幅場景是:弟媳在燒紙,病房走廊裏的兩排座椅空蕩蕩的,沒有一個醫生和護士,而父親的臉上已經被蓋上了白布。
這個時候的翁強顯然還不相信這是事實。他即刻找到一個曾經與自己有一面之交的中醫大夫,讓他幫忙給已經蓋上白布的父親插上了呼吸機。之後,翁強的父親翁文輝竟然“復活”了。之後的6月1日11點58分,翁文輝住入了哈醫大二院ICU病房。
同樣是在這一天,翁強邀請了北京朝陽醫院的院長王辰教授去哈爾濱會診。
“他們並沒有坐什麼專機,誰也沒有本事説坐專機馬上就能坐上的。另外,不管是誰要我去國外買藥,我都會買,為了父親的生命,我不在乎錢。這個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買的藥去了哪?誰能告訴我這個?”翁強這樣説道。
根據翁強表示,患者在ICU住院期間,家屬根據ICU主任于玲范的通知,在66天內從國外共計買回藥品達400多萬元後,每次將藥品都交于ICU的主治醫生和其他值班醫護人員,大部分藥品ICU都出具了手續。
翁強認為院方問題嚴重
根據自己手中掌握的住院病人預交金單據32張和ICU醫生收取病人的自購藥品收據,翁強認為,哈醫大二院有嚴重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7月5日到8月4日共30天時間裏,輸液量為1080113ml,其中減去血慮475642ml以後,輸入患者體內的液體總量仍然高達604471ml,日平均輸入血管的液體量高達20149ml,液體總量在30天內已經達到一噸。7月12日,液體總量149099ml,除去血慮的45000ml,當日輸入患者血管內的液體高達104099ml。7月 13 日液體總量166105ml,除去血慮的69247ml,當日輸入患者血管內的液體總量高達96858ml。7月25日液體總量78604ml,其中血慮35140ml,當日輸入血管內的液體總量達43464ml,根據特護記錄實輸入液體量則為5925ml。不是偽造是怎麼來的?7月30日液體總量86192ml,其中血慮46100ml,當日輸入液體總量高達40092ml,根據特護記錄實輸入液體量為11075ml。
翁強對記者表示,患者8月6日淩晨2點去世,住院費的收取和出院日期竟然寫到8月12日。8月8日和10日,仍然繼續檢查和收費。另外,根據翁強的説法是,不交錢院方就停止治療和用藥,無論每次交5萬、10萬、還是25萬,總是在一兩天內通知錢已經用光。記者在交錢的32張收據上看到了患者家屬不停交錢的記錄,還有醫院不同模式的8個收費財務章。
第三,翁強認為,哈醫大二院重復檢查,編造化驗單,檢查單和血庫項目明細表共3014次。其中,而患者66天住院期間,共查血糖588次,平均每日查血糖9次,患者沒有糖尿病史。66天內查一般細菌培養加藥敏163次,平均每天2.47次,而細菌培養和藥敏需要3天才能出結果,以便醫生對症治療。66天內腎功能檢查186次,平均每天同時查3次(急診檢查一次,生化室一次,再查全生化一次)。生化系列66天內查了68次,僅此一項收費16728元,另外在兩處科室同時查的腎功能又花費人民幣7146元。這三項加起來 66 天收患者費用23892 元。66天內凝血象在急診檢驗科和檢驗室共檢查63次,收取費用6300元。66天內靜脈輸液治療費1843次,相當於平均每日給病人穿刺27.9次,僅靜脈輸液費用高達4405元。化驗單收費總數為2975次,送回科室內的報告單數為2797份,收費單比報告單多出128次。每天用吸痰管328根,相當於4分鐘吸痰一次。
第四,ICU病房的監護儀收費國家規定每天收費人民幣240元,該科室將其分解為4項後,每日收費1248元。在7月�日的某些醫囑上出現院內會診20次,7月�日的醫囑上出現院內會診10次,這些院內會診在醫囑上都標明邀請了什麼科室會診,在當日的特護記錄上卻沒有記載有專家會過診,可是均收取了800元的會診費。ICU危重病人使用液體泵應當每日收取使用費人民幣5元,但是該院卻按照小時收費,而且每天收費高達99.8小時,共收取6485小時,合計金額32425 元。
第五,珍怡,一種生長激素,為腫瘤進展狀況的患者和嚴重全身感染的危重病人禁用的藥物,而院方在明知患者為禁忌症患者的情況下,卻從6月1日開始給患者使用該禁藥達11支之多。
本報記者多次聯絡尋找,截至發稿前,仍無法聯絡上翁強指控的主要對象于玲范醫生進行採訪核實。
中紀委:“天價醫藥費個案”一定追究到底
從開始的中紀委、衛生部聯合調查小組已經升級為中紀委監察辦、國務院糾風辦、衛生部、黑龍江紀檢四大部門聯合調查,調查的級別不斷上升
本報記者馬曉華發自北京
“關於天價醫藥費事件,不會不了了之的,誰該負什麼樣的責任,我們一定追究到底。”中紀委調查組的一位成員3月16日在電話中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從2005年的11月份至今,已經耗時5個月的天價醫藥費調查,結果一直沒有公布於眾。從開始的中紀委、衛生部聯合調查小組已經升級為中紀委監察辦、國務院糾風辦、衛生部、黑龍江紀檢四大部門聯合調查,調查的級別不斷上升。
“調查組沒有公佈結果,到底醫院多收了多少費用,現在還不知道,但是有人説多收20萬元這個數字至少是不對的。”中紀委調查組上述成員強調説。
本報記者一直關注著此案件的進展,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院ICU科的管理混亂,其事實比前段時間新聞媒體揭露出來的更加嚴重,從改病例到改醫囑,病患翁文輝整個就醫過程問題不斷。
患者轉入哈醫大二院心外ICU前的三天
翁文輝,75歲,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臨床醫院住院部二部高幹病房,6月1日轉入ICU病房,8月6日因搶救無效去世。
入住哈醫大二院之後,特別是轉入ICU病房之前三天的檢查中,原本身體其他各項檢查指標都正常的翁文輝,卻在兩個月內告別人世。
此前,翁文輝因腿部發現腫塊,在多家醫院進行病理檢查。其中,2005年4月4日,黑龍江省腫瘤醫院(哈醫大附屬第三醫院)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檢查報告:翁文輝的肝、膽、腎、腎上腺、脾、胰未見異常,胸部未見異常。
2005年5月10,黑龍江省腫瘤醫院進行病理檢查的診斷報告為:(大腿)非何傑氏(Hodgkin)淋巴瘤,傾向T細胞型。
2005年5月10日,哈醫大二院病理會診報告單:富於T細胞的淋巴瘤。
2005年5月11日,哈醫大一院診斷報告:(右大腿皮膚皮下)非何傑氏淋巴瘤,外周非特異性T細胞型可能性大。
“我父親的病是在5月份才確診,在這之前,根本沒有去過其他的醫院治療過。確診之後去哈醫大二院進行化療。”患者的家屬3月16日對記者説。
從住院的病程記錄上可以看到,患者于5月16日下午2點入院,神智清,體溫36.6℃,脈搏84次/分,血壓145/70mmhg,遵醫囑給予內科入院常規二級護理,普食。從記者調查的二部的化療過程中的記錄看,到5月19日,患者在進行化療後,體徵一直處於平穩狀態。
“到了5月31日,化療後我父親的病情加重,轉到了哈二院的心外ICU。”患者家屬對本報記者説,“轉科的事情由醫院的醫生和護士來處理的,根本用不上我們家屬,而且二部距離ICU不遠,只有200多米,進入ICU就如進行手術室,不是普通人能進去的。怎麼可能會有警衛人員,簡直是説謊。”
此前,有報道稱:“翁文輝轉院期間,200米長的小路上,加長的林肯車和數輛奔馳、奧迪車,分別把路口封鎖。幾十名身穿統一制服的保安站在從高幹病房到ICU大門的兩側,以清出道路。病人抬入急救車後,一路無阻地進入了ICU病房。”但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轉科與急救不同,不需要急救車開出去救人,也不要把轉科的病人裝到急救車上,只需要擔架、醫生、護士的護理以及輸液架和呼吸機的隨行即可。
哈二院心外ICU的文化
“6月1日,患者進入ICU後,情況比較嚴重,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到了6月中旬,患者的病情好轉了,當時就想拋開有創呼吸機,上無創傷的呼吸機,因為當時醫院沒有這個設備,所以就沒有用。”翁文輝的原主治醫生王雪原在3月17日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説。
而隨之是大量的腫瘤禁忌藥物珍怡(編者注:珍怡説明書上明確標示腫瘤患者忌用)的使用,400支氯化鉀的大量使用,這些在患者家屬後來蒐集到的治療賬單上都有清晰記錄。
對於非何傑氏淋巴瘤,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種病,一直致力於研究淋巴瘤的江蘇省通州市人民醫院腫瘤科治療方面的有關人士告訴記者:“淋巴瘤並不意味著死亡,淋巴瘤晚期也並不意味著生命的晚期。淋巴瘤現在經過化療和中醫中藥的綜合治療,在我們這裡的治愈率達30%~50%。”
“哈二院出現這樣的事件,也許跟治療目標不明確有關,是沒有與患者家屬溝通清楚導致的。作為醫生,一定要進行目標治療:存活、治愈、致殘、致死,這些都要明白的。”某醫院的ICU專家説。
“我只是知道有些地方不對,但是不知道數字差別會這樣大,我也是在翁文輝去世後,才第一次看到賬單。”作為翁文輝主治醫生的王雪原説,“作為主治醫生來説,我的工作主要是醫療,賬目由主任于玲范和護士長來負責,我沒有權利過問賬目,這與行政安排有關。”
面對成堆的假醫囑、假病歷,作為主治醫生的王雪原感到無奈。
“管理非常混亂,雖然説我名義上是主治醫生,但是我與另外兩個住院醫生是平級的,他們的行為聽命于主任于玲范。雖然覺得他們的醫囑不對,我也改不了。”
據本報記者調查,在ICU工作的兩個住院醫生是于玲范帶的研究生,他們在2005年7月才能畢業,此前,于2005年3月份進入ICU科室進行見習,當時還不具備醫師資格證書。
但是記者卻在2005年6月份到8月份翁文輝的病程記錄上,看到了很多由兩位學生下達醫囑的簽字。
而且,作為心臟外科重症監護室的心外ICU,收治翁文輝這樣的腫瘤患者,也是先前被遺漏的重點:在完全封閉的治療室內,哈二院的心外ICU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科室?
記者從翁文輝的主治醫生王雪原處了解到,他從2001年研究生畢業後就職于哈二院心外ICU,截止到2005年翁文輝患者入住心外ICU,這四年的時間他極少接觸非心臟手術的患者。心外ICU的病人,多數是做過心臟外科手術、在心外ICU過渡的病人。
“我們在這之前幾乎沒有接過非心外科的病人。從2003年到2004年8月份,這一年我們科室是零投訴。”王雪原説。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于玲范收治非心外ICU的病人?
“作為心外科術後的科室,與心血管內科還是有著不同,因為心外科術後的病人,體外循環、呼吸機等有獨特的使用方法。于主任是心血管內科的醫生,基本上與此類病人接觸的比較少,對儀器的使用也不是很了解。”
記者通過調查得知,于玲范2004年8月接手ICU主任的職務之後,到外地考察了兩周,因為ICU的患者比較少,她上任後查房比較少。而她的查房也是比較有特色,把醫生、護士叫到辦公室,把病歷放到桌上,由負責醫生彙報,然後再把病歷看完,提出治療方案,雖然ICU的患者少,但是這個過程從上午8點一般到10點才能結束。而醫院常規的病房床頭查房和交接的流程被于玲范取消了,護士的交接班也不看病人,在辦公室內進行。
“她來了之後把我們以前的床頭查房的程序改掉了。因為她在辦公室進行的查房要進行2個小時,有時病人在叫,我們都去不了。”王雪原告訴記者。
“我在心外ICU工作了4年,見證了三位科室主任領導ICU的風格,前兩位與目前于玲范的風格截然不同。”王雪原3月17日接受採訪時表示。
哈二院的ICU室成立於1984年,是心臟外科術後病人的監護室,為心臟外科服務,主要職責是監測、護理、治療。由於分工越來越細,從2000年10份,這個科室從心臟外科獨立出來,但也是為心臟外科服務。心臟外科每年做的心臟直視手術達1000多例,心臟直視手術的創傷大,所以一般都在心外ICU進行恢復。
2001年的時候,哈二院的主任是孫成光,2003年去世。接手哈二院心外ICU主任的是張衛星,內科學博士、主任醫師。
張衛星現就職于北京大學深圳醫院ICU。張于2004年4月到北京大學深圳醫院,2004年6月份正式從哈二院心外ICU辦理離職手續。
“剛聽説天價醫藥費事情的時候,當時就是覺得作為ICU醫生,第一個要審視自己,第二要問自己也有哪些不對,舉一反三。”2006年3月20日,正在趕往廣州的張衛星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電話採訪。
翁強發家路徑
“作為一個父親的兒子,任何一個人都會竭盡全力去拯救給予自己生命的父親。即使我沒有錢,我寧肯借錢都要給父親去治病。我想任何一個做子女的人都會這樣想。”這句話是患者的長子翁強先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不斷強調的。
針對記者提出的前陣子有媒體稱他與北京某高官有關係的報道,“如果真是這樣,哈二院的醫生還會這樣對待我的父親嗎?”他表示,他找到哈醫大二院最大的官就是醫務科的副科長。
按照翁強自己的説法,他是白手起家,從美容店到服裝,一點點地積累著自己的事業,跟相傳的錢權關係大相徑庭。
“他是一個能吃苦的人,小的時候他的腳趾摔斷了,但是他還是堅持著體育鍛鍊,從來沒有因為這個請過假。”一位與翁強同在當年國字足球少年班接受過徐根寶訓練的人士這樣對記者説。
也許正是這樣的毅力,天價醫藥費的事情才會以這種“激烈”的方式公布於眾。同時,患者家屬也對記者表示,在天價醫藥費公諸於世的過程中,哈醫大二院眾多醫務人員為其蒐集證據提供了幫助。
對於一個醫生,即使受賄1萬元,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嚴懲,前段時間有報道稱,院方多收了20萬元,雖然這個錢數最後還沒有定論,但是即使是20萬元,也足以用法律手段去嚴懲。在醫患關係成為全社會關注焦點之時,天價醫藥費更應該問責到底。
“天價醫療費個案”≠整個醫療界被集體污染
馬曉華
“我最覺得痛心的問題是在我這三年的工作中,還沒能夠把人民最關心的醫療、上學、住房、安全等各方面問題解決得更好。”這是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
溫總理的坦誠讓每個人都覺得一種親近,畢竟醫療衛生行業存在的問題,是客觀事實。但是,無論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都僅僅是“一個事件”,而不代表整個醫療衛生界無藥可治。而醫患矛盾到達極致的事情,更多的是來自於2005年震驚新聞界乃至醫療界的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二院(下稱“哈醫大二院”)發生的翁文輝“550萬元天價醫療費事件”。550萬元,儘管翁文輝的親屬為老人人生最後67天支付的生命成本,因哈醫大二院管理上存在的混亂被多收的醫療費確切數目,還有待權威部門認定。但從這個事件中,暴露了醫療行業存在了什麼樣的問題?給醫療工作者帶來什麼樣的警示?公允地説,哈醫大二院翁文輝事件中個別醫生的失職僅僅是部分人的事情,而不能隨意加到其他人的身上。但醫療衛生行業是否借此反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多數人都很清楚,整個醫療界從業人員的知識水平以及綜合素質水平,都是中國的許多行業無法比擬的。幾乎所有大醫院的醫生都是經過5年本科或者是更為漫長的3年碩士和3年博士的艱苦努力以及職業醫師資格考試、住院醫師培訓、主治醫師資格考試、教授資格考試以及不斷的實踐,最終才成為一個執業醫生。而且,大多數的醫療工作者都是傾心於自己的工作崗位,為自己的職業而兢兢業業。一個簡單的例證是,在SARS暴發的那段非常時期,正是那些值得我們尊敬的醫護人員用生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安全。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個別醫療工作者的醫德缺失,無法也不應該被認為是整個醫療界的集體污染,畢竟更多的醫護人員每天還在自己的崗位上,用心地為患者解決疾病所帶來的痛苦。
同樣的道理,對於醫療行業來講,天價這個概念,並不是遍佈于醫療行業的各個角落,對於一些特殊的疾病,特殊的護理,比如ICU就只是醫療系統內一個特殊的科室,它的收費代表不了其他醫療科室的收費。而事實上,在天價的背後,絕大多數的醫護人員只是“盡職”,做自己本職崗位上應該做的事情。當然,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醫療行業的信息不對稱,給患者和家屬帶來了很多的困惑,而信息不對稱,同樣也是我們現在所無法立刻改變的,因為並不是也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成為醫學專家,而作為這個信息的掌控者──醫護人員──只要儘量用通俗的語言,給病人解釋大概的治療預期結果,就應當被視為盡到了其應當承擔的職責。
從整個翁文輝事件中初步處理的結果可以看出,哈醫大二院的某些工作人員顯然應當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不僅表現在醫囑混亂、病程記錄造假,還有醫護人員的失誤等令人失望的事情。不過,就現在而言,我們應該做的應當是去分析這些問題的背後原因。並且,從哈爾濱天價醫藥費這個事件中找到那些應當成為整個醫療界共同汲取的教訓:對於從業者而言,應該思考如何規範自己的職業道德,而衛生政策的制訂者應該思考如何完善醫療體制,對政府而言,應當思考如何監管醫院。
衛生部呼籲給醫護人員公正評價
本報記者馬曉華發自北京
昨天,衛生部發言人衛生部辦公廳副主任毛群安在新聞發佈會上,對哈爾濱二院“天價醫療費”事件作出回應:“關於自費購藥的數量,調查組的調查由於患者及家屬不能提供充分的證據,關於購藥的數量、渠道、依據方面提供充分的證據,所以,自費購藥的數量不能定論。”他呼籲公眾給醫護人員公正、公平的評價。
毛群安説,目前醫務工作人員的壓力很大,出現質疑醫德的輿論,和當前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其中的一些政策、體制有關係。
前段時間,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的媒體連續報道了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二院患者翁文輝的醫療糾紛事件,暴露出醫院管理以及醫療體制、醫療衛生政策在某些地方存在的問題。
哈二院某專家表示:“從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我們每個醫療人員都應該反思,多多少少醫院是有責任的,這樣審視自己,反思自己做對了還是做錯了,要對得起自己的職業原則。”
“天價醫療費事件給醫療界抹了黑,現在患者的懷疑給醫療界增加了很多程序。無論是醫生還是護士,他們的本職工作已經很重了,幾乎沒有時間處理這些事情。”北京市某醫院的外科大夫昨日告訴記者。
毛群安也呼籲,希望公眾能夠更多地理解醫護人員所從事的特殊工作。醜化醫務人員的輿論會直接影響醫療服務的質量、安全,也影響到醫務人員在醫療活動中的行為。
責編:劉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