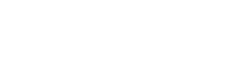中國美學如何支持了當代“國潮”?

舞蹈詩劇《只此青綠》劇照 王徐峰 攝
■劉成紀
在剛剛過去的端午節,河南衛視推出的2022 “端午奇妙遊”活動中的舞蹈《王風·採葛》等作品,又讓國風撲面而來。反觀今年的央視春晚,舞蹈《只此青綠》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也藉此將近年來由《唐宮夜宴》《洛神水賦》《龍門金剛》等舞蹈作品引發的藝術“國潮”“破圈”等話題推向高潮。那麼,這些作品為何能將中國傳統繪畫(雕塑)藝術轉化為舞蹈?中國美學傳統又如何為這類藝術“出圈”提供了支撐?下面試作回答:
“圈”從何來?——近代以來諸種限界的形成
今天,我國美學和藝術界常常談論藝術的“破圈”或“出圈”問題,這種圈表現為中與西、古與今、雅與俗以及諸多藝術門類之間的分離和對立。但在筆者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事實上並沒有在相關問題上設置界限和障礙,也即這個“圈”並不存在於中國歷史中,而是存在於當下人的頭腦裏。很多時候,往往是我們所接受的現代教育導致了一種“畫地為牢”“自我設限”的思維方式,而並非研究對象之間果真存在這種壁壘。
首先是在中西之間。近代以來,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和藝術特性的尋找,往往是以中西之間的差異化比較為前提的,即中國有什麼則西方必然沒有什麼,反之亦然。比如人們一般認為,中國藝術重表現,西方藝術重再現。但事實上,中國藝術也重再現,像孔子就既講“詩可以興”,也強調它“可以觀”;中國繪畫看似輕工重寫,但它對摹寫對象內在意蘊的揭示,卻將再現對象從事物的外觀形式推進到了本質層面。舞蹈藝術也是一樣。現代以來,人們總習慣於通過中西比較強化中國舞蹈的中國性,但卻因此忽略了舞蹈作為全人類共同的身體語言,更多顯現的是跨文化的共通性,否則也不會有可以東西方共用的“舞蹈”概念。由此看來,在研究和創作中更多注意這種跨文化的藝術普遍性,可能比差異辨識更重要。這也是借助藝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義所在。
更嚴重的問題是,當學者或藝術家以中西相異的側面為中國藝術定性,極易導致對中國自身傳統認知的片面化。也就是説,這種傾向只注意到了中西之間的局部差異,而忽略掉了兩者共通的更大部分。這就像一個“再現”根本無法説明中國藝術的全部一樣,對差異的強化也必然會導致無法有效認識中國藝術的全部風貌。在此,如果因為西方的反向限定而自縛手腳,喪失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開放性和普遍價值的把握,就顯然得不償失了。
其次是在古今之間。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中國的建立被先在地設定為與傳統的對立,由此造成了文化激進主義者的“逢古必反”現象。這很大程度上阻塞了中國歷史傳統向現代價值生成的通道。由此導致的後果是,在現代學術話語中,“中國”往往成了一個歷史概念。比如今天一談中國美學和中國藝術,已天然地預示著它指的是中國古代美學和中國古代藝術。這顯然是把“中國”概念強行擠壓進了歷史區間,並因此成為現代藝術的對立物。從哲學上看,這種認識顯然忽略了中國美學和藝術精神跨越古今的永恒價值,看似保護了傳統,但卻因此使其僅具有遺産價值,難以直接成為當代生活的參與者和建構者。
第三是現代知識分類體系造成的問題。中國現代知識分類法是近代西學東漸的産物,它拋棄了中國傳統的禮樂、六經、四部分類,而採用西方更趨細密而嚴苛的分類體系。就藝術史而言,這種西方或現代分類法並不符合中國歷史本身的狀況。比如詩樂舞,在中國歷史中同屬於一個“樂”範疇;在詩樂舞和詩書畫之間,人們也更樂於尋求它們的一體同源關係,而對差異化分析缺乏興趣。
這樣,以西方現代知識分類體系介入中國傳統藝術研究的過程,就成為對原本相對混一的藝術史進行拆解和重組的過程。這必然導致藝術史的碎片化,從而破壞了中國藝術總是在分中求合、異中求同的傳統。這反過來提醒當代的藝術研究者,如果既要使用現代視角介入中國歷史,又要儘量保護歷史現場,就必須在現代知識分類和中國傳統藝術觀念之間尋求協調,以免解釋了歷史也誤解、甚至歪曲了歷史。
據此,“破圈”這一熱點話題,在涉及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轉換方面,可能就需要首先思考三個問題:一是中西之間的差異化比較,是否會因過度強化中國藝術自離于西方之外的獨特性,而導致對其兩相通約部分的遺忘;二是人為製造的古今分離,是否使求新的前提成為拒斥傳統,因而阻斷了中國藝術向現代生成的通道;三是現代藝術分類方式的西方化,是否割裂了中國藝術,遮蔽了它總是在差異中尋求會通的傳統。

《唐宮夜宴》劇照 河南廣播電視臺全媒體營銷策劃中心提供
“破圈”何以可能?——中國美學的理論給予
目前被稱為“國潮”的舞蹈作品,如《唐宮夜宴》《洛神水賦》《龍門金剛》和《只此青綠》等,創作靈感均來自於中國古代名畫或雕塑,如《洛神水賦》之於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唐宮夜宴》之於張萱的《搗練圖》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圖》,《龍門金剛》之於龍門奉先寺雕塑,《只此青綠》之於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等等。在此,“破圈”主要表現為中國傳統空間藝術(繪畫)向時間藝術(舞蹈)的轉換。畫中人物和山水被以舞蹈的形式活化,從而賦予了原本靜態的藝術以活躍的動感和生命。
在現代觀眾眼裏,這種傳統空間藝術向時間藝術的幻化和挪移,本身就使相關舞蹈作品充滿魔幻和奇觀性,從而對人構成吸引。再加上舞者藝術表演的生動高妙,更增加了作品的魅力。那麼,為什麼在現代藝術創造中,中國藝術家能實現這種幻化和挪移?筆者認為,這固然與現代舞臺對聲光影技術的運用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卻是中國藝術在觀念層面並不存在兩者的分離,而是賦予了詩樂舞和詩書畫內在的互通性。
這種互通或一體性,可以從中國傳統書畫理論及美學觀中見出。如南北朝時期,謝赫在其《古畫品錄》中提出繪畫“六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法就是“氣韻生動”。在中國美學史中,“氣韻”本來是一個關於樂舞的概念,但從謝赫始,它卻成為中國傳統造型藝術普遍遵循的法則。這意味著中國繪畫雖然以靜態的形式呈現,但在本質上卻是富有樂感和旋律的,這種內在的樂感賦予它從造型藝術向樂舞藝術生成的潛能。可以認為,上面列舉的“國潮”作品之所以能夠實現從繪畫或雕塑向樂舞的轉移,根本原因並不在於現代人的奇思妙想,而在於它依託的繪畫本身就具有樂舞的潛質。
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如上“國潮”作品均是以繪畫向樂舞的轉換為共同特點,但採取的路徑仍存在重大差異。比如,《唐宮夜宴》《洛神水賦》等作品依託的歷史名作均是人物畫,它的創作路徑是將畫中人物挪移為舞蹈中的人物。而《只此青綠》不同,它依託的《千里江山圖》是山水畫,創作路徑則是將自然山水幻化為人物。這就涉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
在中國藝術史中,廣泛存在著人與自然交互的話題,如梁祝化蝶、《孔雀東南飛》等均是這方面的傑作。在道家思想裏,人向自然的生成也是大趨勢,如《莊子·齊物論》中的莊周夢蝶、《莊子·至樂》中滑介叔“柳生其左肘”的故事,均是如此。莊子把它稱為“物化”。以此為背景,漢代儒家發展出了“天人同構”理論,認為人的每一個器官均在天地之間有相應的匹配物,如人有頭足自然有天地、人有雙目自然有日月等。這樣,人與自然就成了同形同構關係。到三國時期,徐整在其《三五歷記》中記載了盤古之死,説他死後身體化成了大地上的山川河岳、草木金石。根據這種化生關係,人向自然的全面生成,反向也使自然天地人體化,使山川河岳成為人體的映像形式。
後世,這種人與世界交互生成的觀念深深影響了中國藝術,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談山水畫:“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髮,以煙雲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媚。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山水之佈置也。”在這段話中,郭熙雖然是在講自然山水,但山水卻以血脈、毛髮、神彩、秀媚的人體形象向人映顯,自然界的山山水水由此都活化出了人的音容和幻影。具體到舞蹈藝術而言,它如果能把這種自然山水向人生成的邏輯揭示出來,所謂的人舞也就是自然山水之舞。據此看《只此青綠》,它不但將靜態的繪畫轉換為動態的舞蹈,而且進一步將山水轉換為人物,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傳統山水畫本身就是人性和人體的映像形式。這種潛存于山水之間的人體幻影,使相關的舞蹈表演充滿了迷幻色彩,但觀眾並不感到不可思議,這離不開中國美學在如何看待人與自然關係方面給予的理論支持。
“青綠”只現山川?——“文人山水”與“帝國山水”
近世以來,中國人對山水畫的理解,已基本甩脫了它與自然界真山真水的關聯,認為它存在於真實的世界之外,皆“靈想之所獨辟,總非人間所有”。這種能夠表達文人自由心靈的山水藝術,人們把它稱為“文人山水”。但從中國畫史看,傳統山水畫固然有文人“因心造境”的成分,但寫實仍然是其大宗。這就像宗炳在《畫山水序》中,一方面講它是畫家“澄懷味象”的産物,但另一方面也講它“以形寫形,以色貌色” ,即逼真摹寫自然山川仍然是這門藝術得以成立的基礎。
除了表現自由心靈和摹寫自然山川,這門藝術另一重要的情感面向是對自然山川的禮讚。歷史上的中華民族是農耕民族,幾乎其一切財富均來自於自然的饋贈,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借助藝術表達對土地山川的感謝之情,並在哲學上將天人合一作為最基本的看待自然的理念。以此為背景,由於土地、山川、自然對於中國人而言如此重要,它的價值也進而向倫理、政治提升,從而生發出山川神聖的觀念。這一觀念使傳統中國人習慣於用“江山”“大好山河”等來稱謂自己的國家,而相應的審美表達則是“江山如畫”。
由此看來,在中國畫史中,雖然現代人習慣於在心靈層面為山水藝術定性,但它卻是一個價值綜合體,其中包含了山川摹寫、山川禮讚、山川神聖等連續的觀念。尤其當它作為“江山”被賦義的時候,則必然會導出中國這種藝術的政治性。比如,按王紱《書畫傳習錄》,明太祖朱元璋初定天下,曾命令宮廷畫家周位畫《天下江山圖》,周位表示婉拒,因為在他看來,天下江山並不是他的畫筆所能描繪的,真正的畫家應該是朱元璋本人。他所能做的工作也僅是在帝王“摹劃大勢”之後,稍作潤色而已。這裡提到的山水,顯然不是文人式的心靈書寫,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山川圖繪和禮讚,而是要呈現帝王一統天下的雄心和宏業。我們可以將這類山水稱為“政治山水”“王朝山水”或“帝國山水”。
在中國畫史中,起碼在元代文人畫佔據主流以前,以山水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大多具有這種意識形態性,尤其是其中的大山大水之作,更是如此。其中的金碧山水和青綠山水,則具有為無限江山裝飾並賦予華彩的性質。這種政治主題遍佈于從展子虔的《遊春圖》到李思訓的《明皇幸蜀圖》等隋唐作品中,到北宋達到高峰。如美國漢學家班宗華對李成《晴巒蕭寺圖》等作品的評價:“從這些作品的結構佈局看來顯然描繪的是李成理想中的宋代帝國……畫的結構佈局就像龐大的中華帝國一樣井然有序、清澄平遠。 ”而觀賞郭熙的《早春圖》則“類似目睹了一場帝國大夢”。
在這種背景下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可以説它的政治意味更加顯明。在中國歷史上,宋徽宗是一位藝術家皇帝,並尊信道教,但這並不能遮掩他的政治雄心,像聯金擊遼、重鑄九鼎等均是這種雄心的現實表現。王希孟作為院畫畫家和他的得意門生,他的職業本身就具有以圖畫服務於帝王政治夢想的性質。他的《千里江山圖》之所以深得宋徽宗讚賞,則大抵是因為他以藝術方式配合了徽宗的相關夢想。這裡且不説畫中呈現的山勢綿亙、水天一色的壯麗氣象,單是“千里江山圖”的“江山”二字,就已經天然地關涉于當時的王朝政治和家國意識了。
《千里江山圖》是以“青綠”形式呈現的帝國山水。這也證明,它像李成、郭熙的相關作品一樣,都是那個時代具有典範性的主旋律作品,具有從山川摹寫、山川禮讚、山川神聖到山川政治等連續上升的精神內涵。由此看《只此青綠》之所以成為今年現象級的舞蹈作品,除了它在山水與人物之間互化帶來的奇觀性、舞蹈語匯的審美價值,更在於它的“江山”主題與當代中國人的家國情感形成了暗通。而它之所以能登上央視春晚,則是因為它和春晚審美風格上的宏大敘事、價值觀上的主旋律特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如何真正“破圈”?——無界的藝術與限界的終結
以上,我們分析了中國美學對於當代“國潮”的支持。總體而言,這類作品的成功並不是因為它衝破了中國傳統而顯現出創造性,而是相反,即它更深邃地回歸到了這一傳統之中。這中間,如果説當代藝術有種種的“圈”需要打破,那麼首先要打破的就是習慣於在中西之間作差異化比較的傳統。這種非此即彼的自我確證和建構方式,看似守護了中國藝術,事實上卻恰恰遏制了它的多元性和開放性。
在中西古今之間,雖然人們習慣於做辨異工作,但只要相信人類有共同人性存在,各方的趨同性就永遠大於差異性。同樣,人們也總習慣於在不同藝術門類或藝術與非藝術之間設置界限,但它們之間的互通性也要遠遠大於分離。這意味著在當代藝術領域,種種“圈”的存在並不來自對象,而是來自人的自我設限。這就像當代學者總愛強調中國美學和藝術的中國性,但事實上,傳統中國是一個無界的概念,它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從來不認為自己僅僅屬於中國,而是屬於“天下”。就此而言,中國傳統美學和藝術可能表現出了比現代更鮮明的世界性和人類視野,其藝術創造也因此更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義,反而是有些現代人用種種自設的“圈”將自己套牢了。
(作者係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