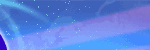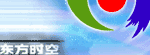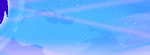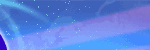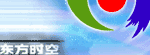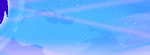|
| 04.02 16:28 |
 |
●張利生
無論人們把紀錄片劃分成多少種類,但紀錄片的紀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當我們用活動的影像去紀錄人以及人們身邊發生的事件時,我們就會遭遇一個必要的前提--與被攝對象的溝通。這種溝通的程度基本上決定了紀錄程度的深淺,或者説關乎著紀錄的成敗。
從心理方面的感受來説,攝影機的鏡頭等於一隻碩大而冷靜的眼睛,這只眼睛不僅常常盯著你,而且還把你所有的言談舉止,想要表現的和不想表現的各種意識到的和下意識的動作毫不留情地紀錄下來,一個普通人或者一個並不普通的人,通常都會對此存有戒心,過去有些少數民族就忌諱你拍他的照片,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魂魄會被攝走。早先拍電視新聞時,一個領導幹部在萬人大會上侃侃而談,而當會後你把鏡頭朝他一對,沒準他就變得結結巴巴的,三分鐘以內汗也會順臉而下,他雖然不怕你攝走魂魄,但他怕哪句話説錯了影響他的形象。鏡頭這東西,確實是帶有某種侵略性的。即使我們這些經常用鏡頭與人們打交道的人,一旦被別人的鏡頭對準了,也還是沒有躲在鏡頭後面去拍別人自在。何況那些對鏡頭不怎麼熟悉的人呢?
從對別人生活介入的角度來説,你是一個不期而至的生人,一個來意不明的窺視者。你所宣稱的好意僅僅只是可能性之一,誰知道是不是還另有所圖?即便你是好意,別人會不會對你拍的東西産生誤解?雖然你紀錄的是人的真實生存狀態和情感狀態,但由於世道上的一些人心險惡,利益衝突,人們並不願意把自己全部真實地暴露出來,而多是躲在某種面具的遮蔽之後,裸露靈魂的不適肯定大大超過裸露軀體的不適。在一個如此複雜的社會裏生存,人們不可能沒有顧忌和雜念,誰也不期望自己能夠天使般地透明。而你和你的鏡頭,恰恰是要和盤托出被攝者的本相。換位思考一下,你就會理解:無端地信任一個不請自到的陌生人,並且若無其事裝做身邊好像並不存在一個無處不在的拍攝者該有多難!
當我們自己理解了這些難度後,便開始有了與別人溝通的心理準備。在爾後的溝通過程中,情感投入是貫穿始終的。情感投入程度直接影響著溝通的深淺。
與拍攝專題片不同,我們不能先自家訂什麼個框框,甚至有個什麼腳本,按部就班地截取些與之有關的材料,然後按計劃裝填進去,製成一個完全表達我們主觀願望的片子。拍攝紀錄片至多不過有個大致的原生狀態,假以時日,紀錄捕捉這種存在演化和變遷,而且在此過程中不斷修改和校正某些主觀的想法和意圖。
既然我們選取了一個關注的對象,就勢必要尊重他的人格,理解他的性情。人心是很靈敏的儀器,攙不得一粒砂子。任何形式的虛情假意,即便用最優美的外殼來包裝,也難以騙取別人的信任。只有在平等的視線裏,呈現你的坦率與真誠,被攝對象才能在確定後把你當做朋友,才能在你面前流露他的真性情,讓你了解他的真實生活。
過去在地方檯工作時,拍攝一個有關時裝模特的節目,有位當時還在高中讀書的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總覺得她有些與眾不同。後來了解到她是猶太后裔。當時我弟弟是家旅行社的翻譯,經常接待一些國外的文化團體。他告訴我,搞學術研究的特別是人類學研究的,對猶太后裔很感興趣。只是由於牽涉到國際上的一些敏感的民族問題,是不準他們採訪的,既然有學術價值,我就有意識地找這姑娘的父母聊天,了解一些情況。他們説他們的祖先大概宋朝就遷過來了(現河南開封有猶太后裔資料館),而且他家的地位還比較高,已經著手把這一枝七家八姓的家譜修得比過去完整多了。數年前這位姑娘大學畢業後,在工作和情緒方面遇到問題時,我也曾幫過點小忙,因此她父母漸漸地把我當成了朋友。他們説曾經有好幾撥人找上門來想要拍片兒,都被他們拒絕了,因為言談話語之間,讓他們覺得有些人主要想拿他們賣錢。他們表示:如果政策方面允許拍的話,會讓我拍他們的真實情況,因為信得過我。再往後,這家人搬到外地去了。片子雖然沒拍,但這十來年交往形成的信任是重要的。
到朱仙鎮拍攝《年畫軼事》時,木版年畫的這家傳人住在鎮西邊的趙村。這種興于唐宋,盛于明清的手工刻製的套色木版年畫,傳到他這一代也可能終止在他這一代。由於政治的、經濟的、審美的等諸方面原因,它成為民間工藝的絕唱幾乎就是必然的。張廷旭從父輩那裏學得這門手藝,靠著它把自己的家境從村裏最窮的一戶變成收入較多的上等人家。但也不過每年比別人多掙幾千元刻板、印刷的辛苦錢,其實家裏沒有幾件像樣的傢俱,並不算富裕。兒女們各有主張,對繼承這門不足以讓人發家致富的手藝沒多少興趣。倒是老外們陸陸續續地有近五十來人先後前來采風,國內的新聞媒體也蜻蜓點水似的有過報道。張廷旭身高大約一米六O,人是極聰明的,既自尊又自卑,屬於較為敏感的那種。剛去拍的時候,我雖然講了來的意思,他還是按照以往的習慣很敷衍地重復著説熟了話和做熟了的動作。我當時也缺乏拍攝此片子的經驗,片斷地撿著稠的撈了一些,鏡頭和剪輯思路以展示他的日常生活為主。後來看看片子太平,折回頭又去拍,慢慢地由關注他的刻呀、印呀的事情轉向關注他對生活的感受和對兒女們的打算。第一次去拍時,是由縣裏和鎮裏的人陪著去的,後來是自己直奔他家裏,在他家裏吃、住。一來二去的時間長了,彼此就少了忌諱,聊天和拍攝的內容也就寬了些。有次他説,他要是個能長得高些,絕對不至於只是現在這樣子。他在一家麵粉廠當過出納管過賬,沒正式學過木匠,但在市裏一個單位做木匠活兒被定為三級師傅,在村裏做過隊長,人緣挺好,誰家的縫紉機壞了都會找他去修。就是個頭太低總覺得自個兒出門不夠排場,也就認命在家裏忙活年畫了。他説有的新聞記者來拍東西,凳子也不敢坐,水也不敢喝,還嫌家裏太亂太臟。碰到這號,他就乾脆説農活太忙,沒空印畫,一推二六五,讓他立馬走人。"我最怕被別人看不起嘍,誰嫌棄我們,我就不跟他配合。反正靠手藝吃飯,年年起五更搭黃昏印上十幾萬張,放在家裏都不愁批發戶上門買走,你報道是五八,不報道是四十,盡給我添麻煩。"張廷旭平日裏待人還是很謙和的,拍攝時也較為合作。我儘量少干預少耽誤他的活計,閒下來時還跟他學學印畫,幫他在些小事上出出主意,為了擴大精品年畫的銷路,他的合作夥伴與他商量印製年畫故事集,上面是畫,下面是説明文,讓人很方便就能明白每幅畫的典故。我提出在字行之間加印信箋式的紅線格子,以增加色彩對比和裝飾感,被他們採用了。另外我還告訴他,我可找人投資,在北京設立一個年畫作坊,資助他的一個子女上學進修民間藝術專業的想法。雖然畫餅難以充饑,他畢竟能體會其中的好意。在近兩年的陸陸續續的拍攝中,有句話經常挂在嘴上:張老師,你説咱咋拍吧。我會對他一句,咋活動就咋拍。
尊重被攝者的人格,與其説是個方法問題,不如説是個立場問題。你這裡先將自己的心給放平了,沒有高人一頭,乍人一膀的感覺,不自以為是的去幹予別人的生活,不用自己的價值觀去代替別人評判,而是開誠布公地尋求一種合作的關係,甚至一種類似哥們兒姐們兒或親人般的關係。自己把人做好了做的節目才會有戲。
異地拍攝時,不止一次地聽到人説,哎,你這個人沒有架子,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要端個什麼架子,擺個什麼譜呢。無論你頂多大個牌子,到頭來還得靠節目説話。三峽拍攝地有個老兄弟開始老是躲著我,但我拍攝的事情偏偏又跟他有直接關係,他負責那塊業務,而且在那個節目中他還是個主要角色之一,但急又急不得,我只好先從外圍拍起,跟他周圍環境裏的人打交道。時間久了,也就慢慢地相互熟悉了。我問他為何前段時間總跟李向陽似的難找。他説他是被嚇怕了,一個拍新聞的哥們兒來採訪,他陪著前往天坑地縫,三角架好像就那樣義不容辭地落到了他文靜而瘦削的肩上,一天下來,十幾裏山路爬上爬下地張羅。你想他在這帶大小也是一當官的,哪吃過這種苦頭。第二天肩膀就紅腫起來。從此,一見到拍電視的趕快就溜,他是被哥們兒的架子嚇怕了。
另一次我奉命去跟拍一個挺有個性的人物,恰好與其他頻道的一位仁兄同行,他也要抓住這個人做些文章,這仁兄是個老電視了,挺敬業的,就是話有點大。幾個月下來他做了二期節目,卻把拍攝對象得罪了。那人到那位仁兄的製片人那兒告狀,説對他跟對下人似的,喊過來喝過去,還好像給了他好大的恩賜。雖然這節目對宣傳他的事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他卻還是不買賬,因為傷了他的自尊了。你説這位仁兄值不值,香也燒了,神兒也得罪了。
拍錢浩亮的兩位同事顯然就棋高一招。錢浩亮因文革中的某些干系蹲過監獄,後來就不大願意説話,他的夫人不離左右地伺候著,同時在他偶爾説話時還替他把關。他們開始造訪這對夫婦的情景恰如《紅燈記》裏鳩山的一句唱詞:"幾個釘子碰回來"。但這兩位同事很有耐心很有韌性。幾個回合下來,冰雪消融,認了乾親,成了自家人--"一股道兒跑的車"。我有幸同他們一起,在錢浩亮家混了頓老兩口親手燒的飯。你想家裏的飯都蹭上了,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對付?
《生命裏的長征》是命題作文,片子主人公是身患腦癌血癌的少校隋繼國,此人37歲。據醫生數年前判定,他早就該陽壽已盡了,然而這個意志堅強的前軍人活得不僅硬朗,還自費到各地遊説,現身説法,號召人們為中華骨髓庫(造血幹細胞資料庫)出錢出力。按説他是自願為紅總會做工作的,但他第二次出行卻早于紅總會宣傳安排計劃月余,這邊想讓稍等一下,一塊行動並推出他,但隋繼國卻覺得有生之日或許已不多,白血病友又急需救助,依然照原想法上路。一路上既有鮮花笑臉也有磕磕碰碰,使他的情緒大起大落。隋繼國是個人來瘋,特善於在人多場合宣傳鼓動,一些政治口號式的句子他説出來讓人聽著也並不很彆扭,而且也有一定的表演意識,鏡頭感挺強。每每把右臂一彎,朗朗對著眾人説:……對得起宣誓時舉起的拳頭。説實話,跟蹤拍攝時,還真讓我挺作難的。即使是主旋律之類的片子,也不大用過去政治口號式的東西,一不小心還是會引起反感。有些時候我覺得他似乎在演戲。走到湖北時,一個在京工作的朋友跟我們一塊吃了頓飯,找個沒人的時候跟我説:操,你拍他呀,幹嘛呢?他老裝丫挺。後來走到深圳時,街頭募捐現場又有一人撇撇嘴冷冷地説,作什麼秀呀?到底拍什麼怎麼拍,路途上我心裏也不太有底,邊拍邊琢磨。好在多是倆人一路上住在一起的機會較多,什麼話題都有。過去我有個搭檔總結了句話,説兩個人如果一塊拍片子同住半月以上(同性),基本上該坦白的就全部坦白出來了。此話果然不虛。三個月下來,他的過去,他的苦衷,他的期望,都碼到了我的記憶裏,當然我這邊的也交流到對方去了。信任這東西也是要等價的交換的。
他有個意思給我的印象最深。明知道治好病的希望很小,才要抓緊時間做事,這事與人與已也都有益處,就算哪天躺倒了,但知名度在這放著,成績在這兒擺著,社會上、組織上就不會把家裏的親屬放在那裏不管。的確也是用心良苦啊。為了病友也為了家人,就算是唱了一場苦肉計,又有什麼不對呢!況且他治病用的藥又有些是屬於自費的,為此背了數萬元的債可他卻又把自己寫的《戰勝死亡》一書義賣的款項一筆筆地捐給紅十字會,就算是演戲,又有幾個願意來演?
慢慢地我理解了他戲後面的真誠,也看到了他戲後面的弱點。這時,作為一個真實的人,他逐漸地在我心中還原出來了。
隋繼國有一個深愛他的老母親,倔強的老父親和四個骨髓配型都跟他不一致的兄弟。小女是他此生的驕傲,妻子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井坤娟在一家學校教書,其堅強自立不輸隋繼國。兩人間有親情更有怨氣。井坤娟本來不願上鏡頭的,幾經勸説才同意,一開口就怨氣沖天。為人媳為人母的艱辛也就罷了,偏偏遇上一個這樣朝不慮夕的丈夫,還滿世界跑著張羅別人的事,不用最後的時間來陪陪家人,別人可能認為高尚,但她卻認定是自私。她是有理由發牢騷的,換了別人,或許早就吹燈拔蠟了。難得她一直還挺著。
我曾説過隋繼國,你到處做好人,哄得老老少少都説你好,就是不哄住自己的老婆。親人説你不好,你那些好還不是假的?他自我解嘲:我倆都是屬免的,可不合適在一個窩裏。她是家兔,我是野兔。
我也曾問過井坤娟,隋繼國這趟從北京到深圳的路走下來,要是再鬧點兒"保爾故鄉行"之類的名堂,你怎麼辦?對著攝像機,井坤娟開始一直是很努力地笑著:跟他離,馬上就去把這事辦了算啦!這時她臉上還笑著,但眼圈已經紅了,眼睛裏濕濕的,是淚。
隋繼國是很要面子的人,井坤娟也是。
節目編完初稿,製片人覺得井坤娟顯得過於厲害了,讓修改。遵命後,我在片中讓隋繼國用畫外音形式向井懺悔:"其實替她好好想想,也真夠難為她的……"
片子播出的前一天晚上,我打通了隋繼國家的電話,是井坤娟接的。後來隋繼國撥電話過來要請我吃飯,我不想無功受祿。那邊他倒得意了:你告訴播出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倆已經收拾好東西,準備分開住了。後來説明早一塊看完節目再分也不遲,等看完節目後,老婆就看在我態度還算端正的這點上,給我留了點面子,説先不分了。再後來她在學校裏又評上了副高職稱,一高興,還用一個真皮手包給我發了獎品。這裡也有你一份功勞哇!
這之後,隋繼國的"保爾故鄉行"陰謀尚未得逞,復發的腦癌就毫不留情地將他扔到了手術床上。術前術後,我各去見了他一次。他缺乏血色的手伸出來,不甘心地在我的手上握了一下。床頭上有幅關係絕對純潔的女戰友的照片,在病床上他也還忙著。給女兒寫遺書悲壯的神情,打電話安慰母親的那份細緻,以及對妻子不在現場的怨氣,比節目裏的隋繼國更有可視性,但這傢伙把形象看得很重,這種關頭還是不去惹他為好。腦殼一側第二次被掀開,他居然又活了過來。他因心大而命大。製片人知道他的事後,派人去慰問了一次,又讓隋繼國有了次小小的得意。片子沒再繼續做下去,但朋友繼續做下來了。這之後井坤娟也打電話説要請我吃飯。這飯,我得吃,要不,他們會説我譜大。
眼下我正在三峽間的幾個點上來回穿梭,拍攝移民和文物保護方面的題材。移民工作據幹部表達是破解世界性的難題,但對移民們來説勢必犧牲諸多利益,其間的關係複雜而敏感。去年年底,我已與拍攝地的人們有了些溝通。不對鏡頭時,彼此可以説些不宜發表的想法。越難越複雜的事情,就越具吸引力,在探險的途中人是興奮與充實的。真誠可以讓人逢凶化吉,得天之助得人之助。
我們在拍攝紀錄片時投入情感,投入熱忱,我們同對方一起面對生活的艱難、困惑和無奈,感知生命的張力,感受情感的波動,體驗每次的挫折與輝煌,於是便有了心靈的溝通,便有了理性的思考,便有了生命的頓悟。我們在對方身上照見自己的影子,我們在自己身上演繹著對方的故事,永遠在別人的故事中訴説的自己的心事。
我們對變遷的時代投入情感。我們對鮮明的個性投入情感,我們對人類的境遇投入情感,我們對深愛的自身投入情感。我們紀錄,我們思索,我們收穫心靈的道白和震撼,我們對已知命運冷靜審視,我們對未知命運無限期待,我們用鏡頭做出時代的影像報告。紀錄片是整個人類命運的關照,紀錄片也是紀錄片人的情感歸宿。
我們是感性的,
因此我們更是理性的。
|
|

責編:李穎 來源:央視國際網絡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