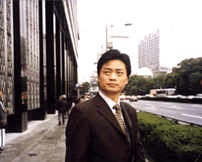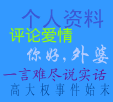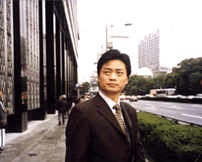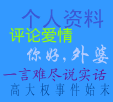|
問:在現場有沒有讓你感到尷尬的時候?
崔:這是我兩年中一個非常大的轉折。我第一次面對全場觀眾感到尷尬的時候,我非常難受,覺得給全國的主持人丟了臉,因為他們都沒尷尬過,就我一個人這樣。後來我仔細想了想,他們都是科班出身,我是半路出家,我不尷尬誰尷尬?東平老師也諄諄教導過我,談話節目的主持人是一個正常人,不是因為學問有多高,長得有多好看,地位有多高或家裏有多少積蓄,就是因為你是一個平民,你有和他們一樣的心態,你們可以平等對話,人家才選你做這件事情。老百姓能犯的錯誤,他都可以犯,只不過他不能以這個為藉口,故意犯錯誤。掌握這麼一個尺度就可以了,以後在現場遇到尷尬的時候,我就尷尬一下,我覺得挺好。
問:具體的尷尬事兒你還記得嗎?
崔:你要早幾個月提這個問題就好了,現在有點晚,因為太多了,根本記不住。我認為每場都有。
問:有沒有遇到有的嘉賓讓你感到壓力特別大,因為他可能比你更機靈,或者棋逢對手,讓你感覺興奮?
崔:越是這樣我越高興。
問:你是否遇到嘉賓給你下套的時候?
崔:不太容易,因為在那個場合我每一個毛孔都在警惕著。一般我都是把他們的背景介紹清楚,公佈出來,他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他是那個領域的學者,和他們相比,我就是一個很淺薄的老百姓,如果他們給我下套,大家會覺得他們"良心的,大大地壞了",你這不是欺負人家孩子嗎?你怎麼能這樣?這個道理他們也一定能想得通。
問:早期節目的嘉賓請了許多名人,但現在大多是普通人,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
崔:我説實話會不會得罪他們呀?
問:説完了再刪。
崔:我們請過名人,也請過老百姓,統計結果表明,名人不如老百姓表現得好。當然是我自己統計的了。名人也許接受採訪太多,曝光機會太多,他們講話時過於考究。
問:把參加這個節目當成表演了?
崔:對。老百姓沒有這個顧慮。我印象最深的是孫大媽,來我們節目之前,不光沒有進過演播室,甚至都沒看過電視。我們把孫大媽蓋的5間大瓦房拍下來,在現場放大在屏幕上,讓大家看看這5間大瓦房有孫大媽多少心血。我想起個興,就問:孫大媽,這5間大瓦房是什麼樣子的啊?我覺得這5間大瓦房讓孫大媽用自己的語言來形容會更生動一些,沒想到孫大媽説:你不是都看過嗎?你還在裏面住過一晚上呢!
問:那時你是尷尬了,還是覺得這種談話方式特別好?
崔:那時候應該説是覺得尷尬。我現在想現場多出現這樣的情況,可是不出現了。以前害怕,可是老有。其實這類情況,只要你能把握,效果特別好。
問:早期和現在的節目中都在請一些專家做嘉賓。請這類嘉賓有什麼作用呢?
崔:如果我們講實踐,需要講三天三夜,講理論的專家一句話就可以把它説清楚。我們請專家是希望他能起到畫龍點睛作用,可以把很複雜的事物概括出來。從實際生活中看,我們的專家在為民服務日,上街攔著你,説要給你測血壓,這樣他就能把血壓高低這個事兒通俗地講給你聽。可是有時到了節目裏,他們把理論通俗化非常困難,雖然話相對短了,但老百姓還是聽不懂,起碼我聽不懂。
問:把現在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那麼什麼樣的談話者是好的談話者?
崔:談話確實需要相互配合,好的談話者可以給你留有餘地,給你鼓勵和信心。好的談話需要放鬆的心態和相互的信任。做
《上學的外婆》時,策劃反饋回來一個信息,説外婆的女兒不喜歡我,説那個主持人很壞,她媽媽不適合做這個節目。做完節目之後我徵求她女兒的意見,她女兒説,通過做這個節目,我改變了對你的看法。通過談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印象。
問:讓談話正常有什麼秘訣,可以公開嗎?
崔:可以,希望人人都能掌握,這是從生活中總結出來的。早先做節目的時候沒有經驗,開始的時候聽見一個尖厲的女聲:準備開始!五、四、三、二、一。這不是正常的談話方式。你想想家裏來了客人,你不會倒上一杯茶後説:咱們開始談話吧,五、四、三、二、一。所以後來我們就在現場還原正常的談話空間。首先談話者要對你有興趣,觀眾坐定之後,我就來一番自嘲、坦白,我希望他們這樣想:這小子沒什麼了不起,跟我們是一樣的。
問:你對話題的好惡會不會影響節目的製作?
崔:這是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年輕人,30多歲,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有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有些事情我明顯地反對,但是這個節目又要求主持人不露痕跡,保持一個中立的立場。現場經常看見我面帶微笑,實際上頭都要炸了,我實在聽不下去了。有這樣的情況。
問:就是説,你不喜歡的話題這個節目可能做不好。
崔:因為幹了2年了嘛,不能像一個野孩子,應該有一點職業的心態溶進來,應該用職業的規範把你的本性變化變化。
問:是不是你像一場球賽的裁判,有時恨不得參加到比賽當中去?
崔:對。有的觀眾也看出了我的裁判水平,在觀眾來信中有的説我吹黑哨,明顯地偏袒一個隊,懷疑我拿了人家的錢。
問:現在許多人反映你老愛打斷別人的話,為什麼?
崔:現場應當瀰漫著兩個字--公平。作為裁判我説的很清楚:打斷是我們的權利。如果不打斷的話,我們都要在這裡守夜。我可以打斷你,你也可以打斷我。打斷可以讓談話有節奏。你還要考慮電視機前的觀眾的耐性。不信咱們可以試一試,做一期不打斷的,我估計觀眾在自個兒家裏就把你給打斷了。
問:有的觀眾問:現場經過排練嗎?
崔:這事兒非常苦。如果硬讓老百姓搞表演,只有一條路:砸。所以我們現場絕對不排練。包括開場第一段話,我希望都是即興的。有時因為技術原因,開場要三次,甚至四次,我説的話都不是一樣的。把同樣的話再説一遍,自己都會很難過。
問:事前的策劃案對你起什麼作用?
崔:策劃案是一種思想。如果談話者不帶著思想去談,沒人相信。沒有這樣一個思想,現場很難張嘴。現在有學者幫我理清思路,張嘴時就會有信心。但從哪兒説到哪兒,那得看現場觀眾願意到什麼程度。
問:有不少人説,現在你的節目有模式化的傾向。你怎麼看,打算維持還是打破它?
崔:我們一直在強調正常的談話,所謂模式是一個人的性格。一個人如果不經歷離婚、分家之類的人生大事,那他的性格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不變。反過來説,觀眾可能就奔你這個樣子來的。比如你愛看京劇裏的一個流派,是啞嗓子的,有一天你進了劇場發現他的嗓音洪亮了,你轉頭就會走。至於其他的表現技巧,那是編導考慮的事,我沒拿這份錢,也不想這個事兒。
問:你覺得這個節目靠什麼打動人呢?是思維的深度還是真實的情感?
崔:我也不知道。如果讓我選擇,我會首先選擇真實。關於包袱、噱頭這事兒,我到現在總是進退維谷。觀眾的反映總是分成兩派,一派説喜歡這個,沒有這個就不看;另一派説,如果沒有這個節目會更好。明明很嚴肅的事兒,讓你把氣氛破壞了。我現在跟大家坦白,我這種談話方式,是我骨子裏的。如果你們非要我改,我就儘量改,實在改不了,只好換下去,沒有辦法。
問:這個節目有時候要有趣,有時候要把道理講清楚,你覺得哪一個更重要?
崔:要是我選擇,我就選有趣。因為講道理的渠道太多了。比如有那麼多的書店,那麼多長進自己的機會,北京圖書館全天開放,你研究什麼都可以看到幾十、甚至上百年的資料,你可以到那裏去做學問。但大家累了一天,辛苦一天,來看看你的電視節目,在這裡做學問,真是讓他們太累了。我還沒聽説誰看電視把學問做成的呢。但是現在讓他們輕鬆的東西不太多,這不是我們的牢騷,説相聲的、演小品的、拍喜劇電影的,現在都覺得越來越難讓老百姓認同了。讓老百姓看完我們的節目很輕鬆,這是我們至高無上的原則,甚至比講道理更重要。
問:這個節目在文化追求上比較重視民間性,這是有意識的嗎?
崔:嗯,我特別強調這一點。我老婆還跟我説這個事兒,她説,你看,走在街上認出你的老百姓都那麼友好,跟你接著談節目中的話題。拍你的肩膀、按你的脖子,這就説明你的節目得到了認可。如果人家都遠遠地盯著你,最多擠上來讓你簽個字、拍個照片,你就差不多離演藝界二流演員不遠了。憑我的基本條件,在演藝圈裏撲騰,也就是個三流演員。
問:問一個更理論性的問題。許多人認為電視是靠畫面構成的,電視語言也有蒙太奇,但一堆人坐在那裏談話,用電視來表現是否違背了電視的本質?
崔:不違背。電視是以畫面構成的,這是有道理的,但是什麼是電視畫面,這值得好好探討。現在一説草原,就拍一片綠草;一説理想,就拍一片藍天;一説老百姓生活,光圈就調低,黑糊糊跟著屁股走。這是對畫面很膚淺的認識。你看看我們節目的現場,好的畫面非常多:有人在傾聽,有人在思考,有人在交頭接耳,有人急不可待要站起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畫面的信息量非常非常大,即使他站起來沒有把自己要説的表達清楚,甚至在節目有限的時間內地都沒有機會表達自己,但我覺得畫面給你的信息量都是足夠的,而且畫面居非常鮮活的,或者説是真實的。把這些記錄下來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樣的畫面有一幀就足以打動人了。
問:你對這個節目對老百姓的生活起什麼作用,有沒有自己的評價?
崔:從收視率看,有成千上萬的人為這個節目早起或者晚睡,這肯定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甚至有人看完了還要給我們打電話或者寫信。所謂作用也就莫過於此吧!我們不能指望一個談話節目就能讓人靈魂出竅,這個想法不現實。
問:但是不少專家認為這個節目意義非常大,因為中國現在還沒有一個地方由專家和老百姓一起就一個公共問題互相交換意見。你同意這種看法嗎?
崔:我懷疑有這種看法的專家所在的單位來了一筆經費,他們要花掉這筆錢,就立了這個選題。我覺得一個談話節目負載不了那麼大的責任,一次講話倒可以。
問:播出的節目和現場比,哪一個更好一點?
崔:我們特別強調工廠化生産。前期的策劃是節目的一部分,現場的主持又是一部分,後面的剪輯讓兩部分昇華。如果剪出來的片子還不如現場好,我覺得這事你該採訪一下這個節目的編導。
問:一個節目要分前期、現場和後期三部分,你對它們在一個節目中對質量的作用大小怎麼看?
崔:要是跟媒介説,應該説各佔30%。要是偷偷地説,現場至少要佔到50%以上,因為主持人現場的發揮直接關係到節目的成敗。節目策劃得再好,主持人現場變成了大傻瓜,這個節目就很傻,後期編導再有本事,也不能妙手回春。
問:不少地方檯也在辦談話節目,有的節目明顯在模倣你,對這點你有什麼意見?
崔:沒法兒説。因為我不能肯定他們在模倣我。比如也找一個長得有點像我,手也放在同一個地方,你無法説那是不是人家的原生態。我倒是覺得我們節目的名字經常受到侵權,不少報紙雜誌都辦一個《實話實説》專欄,不知道能要回錢不能?但這對中國的觀眾來説,肯定是一件好事,我們也能來一番競爭。可是我看他們都不堅持,轉向太快,都往裏揉遊戲、揉小品、揉歌舞,話説得越來越少。
問;每一個電視節目都有它的生命週期,你覺得《實話實説》還能存在多久?
崔:如果説《實話實説》是一個電視節目,它改變不了改頭換面、甚至銷聲匿跡的命運。如果把它視為正常的社會談話空間,那它的生命永遠不會停止。
問:現在有的節目裏,看見你很疲倦。有不少人會擔心,你精彩的東西會不會有一天被掏空?你現在有危機感嗎?你如何再充電?
崔:我想引用兩個人的話,證明這件事我想通了。我和楊瀾有過一次短暫的談話,我説談話節目報要一個人內心真實的東西,讓我做上半年,就會被掏空了。當時楊瀾睜大了眼睛,説:什麼?半年?二期就掏空了。我們的知識哪兒夠用啊!當時給我當頭一捧。後來不久,就見到著名作家麥天樞,我向他敘説自己的苦惱,説自己過去有一個很好的習慣,看看書、讀讀報,現在時間越來越少,尤其是靜下來讀書的時間。麥天樞説:你聽説過這樣一句話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就愣了,我覺得這句話沒必要解釋。麥天樞説:十個人有十個解釋的不對。這兩句話是並列的,就是説,一個人讀一萬卷書和行一萬里路,收穫是一樣的。不是説先得讀一萬卷書,再行一萬里路,那任何人都達不到這個境界了。他説我再給你加上一條:和一萬個人説話。你現在就靠第三條,這和讀萬卷書的效果是一樣的。這讓我豁然開朗,我覺得現在我一直在充電,而且不比誰充得少。
問:許多人説,在看《父女之間》時,看見你哭了,由此改變了對你的看法,原來你還有另一面。在生活中你是一個容易被感動的人嗎?
崔:我堅信一條:我吃長相的虧吃大了。比如打起仗來,我只能是屬於打入敵人內部的那種。但自己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很容易被打動。記得在電臺時採訪邊防部隊,在那裏採訪,邊問邊哭;回來給同事講,邊講邊哭;編輯的時候,邊編邊哭;播出的時候,邊播邊哭。始終在那個狀態,非常容易被感動。這方面的體質太弱。現在著春節晚會,我知道這段又要煽情了,可還是控制不住,被煽得一塌糊塗。
問:看來你心太軟。我們知道有的女孩子在瘋狂地追求你,你心軟過嗎?
崔:有時候會管不住自己,這就要借助外力。我的辦法是,一得到這樣的信息,首先反饋給我老婆,然後看著她拉長的臉,我就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了。我一直覺得這些女孩子不是真心喜歡我,因為我做電臺記者時非常優秀,可是沒有一個人給我寫信。
問:當了主持人之後,生活中哪些事兒方便了,哪些事兒不方便了?
崔:這一點我認為特別值得誇耀:就是我當了主持人之後,我的生活沒有任何變化。和以前一樣,有非常好的心態,常人做的事我都可以做。我可以在夏天穿著大褲衩子抱著我閨女在長安街上走,一切都那麼舒服,沒覺得有什麼大的約束。至於説到方便,謠傳有人要送我房子,但至今沒有和我聯絡上。
問:現在對你交朋友有什麼影響,現在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功利色彩?
崔;這問題一回答又會得罪一批人。我過去交的朋友有很多是有功利色彩的。現在交的朋友自然也劃成兩派。
問;你能分清嗎?
崔:他們自己能分清。可是我身上沒有什麼油水。
問:最後問一個俗的,借這個機會,讓你感謝的話,你最想感謝誰?
崔:回答這個問題又是一個得罪人的事兒,總是會挂一漏萬,説了這個,忘掉那個。感謝所有的人吧,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