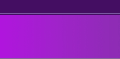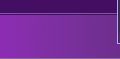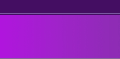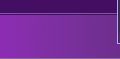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
| 永遠的柴靜 |
是你嗎,柴靜,電視機裏那個有著光潔的高高的額頭的女子,那個清湯掛麵的頭髮不時地垂下遮住面頰的女子,是你嗎?
兩年前,在每個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10點半,我都會靜靜地躺在一邊擠著書,一邊擠著自己的床上,戴上耳機,聽你的“夜色溫柔”,聽那段你讓我在風中苦苦等待,在風中苦苦等待,在等到你的到來,只是告訴我你要走的標誌樂,聽那個沉鬱。安靜的聲音在淡淡的音樂裏讀聽友的來信,聽熱線裏那些稚嫩,無助的靈魂在午夜裏遊蕩的回聲。在我的記憶裏,長沙的夜色並不溫柔,只是冷,冰涼冰涼的月光籠罩著幽藍的校園,縮著脖子唱搖滾的男生,抱著熱水袋三三兩兩往宿舍裏趕的女生,呼嘯的風掠過夜色拍碎窗房玻璃發出的清脆的響聲,還有宿舍裏永遠不會消散的牌局。每一年夜晚幾乎都是如此的匆匆,在我們雖然年輕但終將不會年輕的生命裏。所以,當我躺在床上,眼前一片漆黑的時候,我就感激地想,這位叫火柴的柴,安靜的靜的年輕女子,她又將帶給我一個怎樣溫暖的夜。有著欣長欣長白色的杆兒的火柴,當她燃起的時候,那剎那的微光,又是怎樣去照亮一個霜涼如水的夜啊?
97年的聖誕節,下著小雪,幾位在南昌時的老同學圍著一個小小的火鍋,象校園裏化粧午會上的那些學弟學妹一樣,認認真真地過這個更屬於學生的聖誕節。應該説。我不太喜歡這種大團圓式的聚會,從火鍋的底料聊到房間墻壁上挂著的衣服的品牌,熱熱鬧鬧的;心裏卻是空蕩的遙遠。我抽著煙,看這些六年前已經熟悉的面孔,這些也曾稚氣、生動的面容,現在,在另外一個共同的校園裏,用自己誇張的言語和熱情,彼此歡樂,彼此感染著。他們盡情地揮霍著相隔六年以後,時間賜與他們的智慧和表情。一位女同學忽然説,你們來長沙這麼久,有沒有聽過柴靜的“夜色溫柔”?我詫異起來,因為,印象中的她,是成熟且饒舌的,成熟得近乎圓滑,我們在一起時,除了對她滴水不漏的為人處世有著幾乎絕望的仰慕之外,更多的,則要一些雞生蛋、蛋生雞之類的抬扛遊戲了。她説,那天在烈士公園裏遇上柴靜,個兒高高的,長髮美女;她説,上星期聽夜色溫柔,湖大的一位老師打進5517066 ,説,柴靜啊,你是我們長沙夜空裏唯一的安慰。當時,她用被子矇住了自己的臉,怕哽咽聲驚醒沉睡的人們;她還説,每當午夜零點,那首鄭智化的《讓我擁抱你入夢》響起的時候,她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想,那個同屬於70年代同齡人的聲音,為何如此睿智感性。謝謝你,柴靜,謝謝97年的聖誕節,讓那些心裏隔你很遠很遠的朋友,再次赤裸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思想和心靈。
現在,電視機裏的你,坐在台灣來的蔡琴面前,説,我在做最後一期電臺節目的時候,播放了你的那首《渡口》,然後,我離開了那個呆了七年的城市。你的聲音,依然很有韻味,如同廣播裏傳出的那種,你安詳、隨意的神情,仿佛在提醒自己,這是一段日漸久遠的往事,這是一個渡口。可是,我卻固執地回憶起98年9 月的那個夜晚。我記得,熱線和往常一樣難以撥通;我記得你輕輕的啜泣聲;我還記得,很不喜歡電腦的你把一位聽友為你申請的email 地址告訴大家。一個感覺上和自己風雨相伴的人即將離我遠去,象滴在沙堆裏的水珠一樣,消失得乾淨、徹底而又順理成章。那個夜晚,我又一次感受到那種蒼老的悲涼,這種感覺來得突兀,無法抗拒,久遠而又親切。 後來,楊謹接了你的空檔,標誌樂沒變,欄目沒變,內容沒變,甚至連那曲《讓我擁抱你入夢》也一樣在午夜響起。後來,我也離開了自己的渡口,重新回到熟悉的人群中,過一種安逸、平淡的生活。再後來,我成為一名兼職的電獺狫,和你一樣,在週末的夜裏坐在昏黃的直播間裏,放一些熟悉的歌手的歌,接一些熟悉的感傷的電話。可是,我從沒想過,我會再次聽到你的聲音,而且,能夠真真切切地看你一次、兩次。
人們説,時間象魔術師,侵蝕我們嬌艷的容顏,輕易地擊碎我們所有對未來的憧憬。但是現在,在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現在,我寧願相信,有些東西,時間是難以改變的,比如,相隔山嶽的長沙、校園,還有你,柴靜,還有,我們正在漸漸遠行的青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