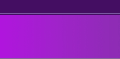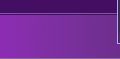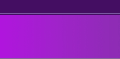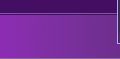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
| 《最藍的藍》 |
那一夜,在上海。
米丘白衣黑褲,長髮。站在蒼老的“四明公所”牌樓面前。
一年前,為了保全它,他將它平移26米。在那周圍設計了玻璃,鋼,清水,燈。雕有各色翅膀,包括水面之下。
上海的聲光色影在其中反射相投。
站在其中的人也沉浸於光線,有隱隱的神秘氣息。
“我也用黃金做過翅膀。”他説。去年他為世界黃金協會設計“生命之骰”,黃金的翅鑲在兩顆水晶上,黑與白。如同輪迴。他説黑水晶是很神秘的,最後制出時模具也隨之毀滅,“又是用來做骰子,想一想……那是一種很宿命的美感。”
那麼多的翅膀,在他看來分別有喜樂哀愁的表情,我忍不住問“你迷戀飛行?”。
“其實,喜愛飛行是為……你見過嗎?那種坐飛機時看到的藍,暮色和凌晨來的時候,那樣的藍。”
他後來的畫裏,試着調過那種藍。
“試了不少次”他説話夾雜着上海腔和一點點英文,有些詞卻用北京話説,異常圓熟。
“大學畢業在北京。什麼都幹,舊城改造,水墨畫,攝影,行為藝術……”
那是82年。他分到建設部。結識的卻是北島陳凱歌一色人,從此眾人行。有次陳凱歌要拍他的一個短片,一行人在天安門,突然狂暴的雨一卷,廣場空無一人,他獨自呼喝奔跑,簡直以狂歡的姿態在天風海雨中趔趄而過。
彼年他26歲。
第二年他們五人被邀去歐洲演講,之後9年,他居留挪威。
從訪問學者到海涅昂斯塔藝術中心的藝術總監。然後是歐中文化交流計劃的主席。
舉辦“中國藝術五千年”大型歐洲回顧展。他用集裝箱從黃河運來了36噸黃土,到歐洲後,清除,吹乾,最後將20噸黃土鋪在展廳裏。
金縷玉衣就懸浮其上。
辦完展覽,閒,日日黃昏時出海,只為看藍色,水面,天光,還有山脈,從藍的深處到更深處。那藍到了臨界點,令人惑。
呵呀。
為什麼要回來此城呢?
他一笑,打住舊事不説,帶我們去爬滿廢藤的工廠改造而成的“1221”吃上海菜,滿廳中西雜陳的人,女人都穿濃紫深綠,或是鏤空蕾絲的黑裙,耳上一粒鑽,細細地夾着煙。
一群人,都是他的朋友,飯後呼嘯一聲,去宋美齡舊居的後花園,重重深綠的藤蔓,夜風吹過腳踝。
他為每個人要酒。那種智利的酒,有藍色火焰。
一夜聲色。
只有他一個人清醒,送每個人回去。
次晨去他郊區的工作室,他穿藍工裝,身上濺滿泥漿,隨坐隨臥。和工人一起在腳手架上爬上爬下。
有工作時,他會在這裡封閉數月,“勞動有一種非常……嗯,樸素的快樂。”他坐在石膏上説。
6月份北京東方廣場前,那座叫做《飄》的雕塑就來源於斯。 黑合金鋼,中性的人體。小而狹的頭部。細而長的頸與肢。有翅自肩打開。失真的比例使它有非人間的氣質。
同時又是均衡,精確。十分物質的。
象他的家。
房子很簡闊,玻璃桌,寬口水晶瓶,沒有插任何東西。簡無可簡。到處是線條。只有流風穿梭。一塵不染。
兩隻沙發,一隻深藍。另一隻白色的,面對闊大的陽臺,在那裏可以看到上海蒼藍的黃昏如何歸於寂滅 —— 看這華美魅惑的城,漸漸去到夜的深處,睡眠深處,靈魂深處。
他開亮頭頂鋼架軌道上的射燈。
我翻看雜誌上他作品的圖片。建築,畫展,攝影……很多以“幸福生存”命句。“技術,或是藝術,都是為了人”他在一旁輕聲解説。我翻到一些的紅色的照片,象一個人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身上。
那是九三年挪威國慶節前,他做的“全球傳真行動”,主題是艾滋病。向世界各地發出2000封信,在3月的兩個星期中,24小時開通的傳真機源源接收着來自世界各地關於艾滋病的答覆,上千件。有美國作家、法國詩人、同性戀者協會的成員和尼日利亞的總統。
5月14日晨7時到次日晚7時,他將那些傳真印刷成紅色,貼在一起,在地面鋪了148米,那條道路的一邊是議會大廈,另一邊,公園的後面就是皇宮,側面是經濟法學院。有將近60萬人從那裏走過。
“那天下雨,紅色的光投在人的臉上,站在那裏,看到那些不同的神色,怎麼説呢……”
他沉默一瞬,站起身去放了《費城故事》的原聲唱片。患艾滋的湯漢斯在臨終前某夜放給丹素.華盛頓的那一段。
“記得嗎?他牽引着那些纏着輸液管子在音樂中旋轉,講述死亡。”米丘抬起臂,手在空中劃出弧線,他的臉在暗處,眼中有光閃動。
歌劇已到結局,弦樂驟起,聲音明亮如黃金。是敬畏,是悲憫,是隱密的喜悅與悲意。我兩頰發麻。人世悄無聲息。
“藝術家,創造戲劇性的時刻”我輕咳一聲,開口。
“或是,感受它。村上春樹,書裏寫,和一個西班牙朋友去吃墨西哥菜。夕陽照來,人滿身通紅。他説坐在那樣的光線裏只能哭泣。”他頓了一下,聲音輕促“看到這兒,我也哭了。”
人,在那樣的光的照耀下,走很久的路,去往很遠的地方。
採訪完回到北京後,有一晚他打電話來,正在他父母那裏,他的兩個姐姐也在。説難得一家人在一起。
“其實當初回國,是因為可以離父母近些。”因為沒有聽他説過這种家常話,我在電話這端愣了一下。這種世俗的暖意是他身上罕見的。
想起他説“調色時永不可能調出在海上看到的藍,那藍,有了光,有奇異的變化,才是最藍的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