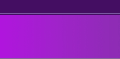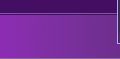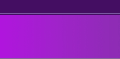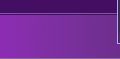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
| 張朝陽:不知道為什麼而奮鬥 |
我對在國內成名這件事有點麻木,可能是生活多元化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彌散化造成的。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呢?在那個群體裏的成功是成功嗎?
一
“很小的時候,我就在等待大事發生。”張朝陽説。
凱賓斯基的咖啡廳裏,我們一人一杯清水,相對而坐。他的臉在明亮的燈光下異常清晰,在一個女性看來,這樣的面容充滿敏感的氣息。
1978年來到了。
“那是科學的春天,又恢復了高考制度,楊振寧、陳景潤是那個年代的偶像。”所以他略帶自嘲地輕笑,“我的理想是關在只有一盞小煤油燈的屋子裏解數學題,一整天只吃一個冷饅頭——當然,那個時候我的確喜歡物理,它對世界作出解釋。”
17歲,他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在那裏度過了5年。
“被傷著了。”他説,“學物理的人非常純潔,所以競爭才格外殘酷。不停地比,比誰的作業先完成,誰學習的時間最長……整個小社會只提供給你一種可能性,所以……我的成績一直是前三名,可是得不到第一名時的感覺……就去遊冬泳,那水真是刺骨……每天繞著圓明園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證明我是可以的。”他搖搖頭。
“現在想想那是很自虐的。”
22歲時,他考上李政道獎學金,“心裏就松下來了,在清華最後一年我過著東遊西蕩的生活,我的任務完成了,證明自己了,那時候我什麼都無所謂了,去不去美國……甚至,當時死了,也無所謂。”
我在驚訝中沉默了。
他仍保留著讀小説的習慣,最喜愛的是《約翰�克裏斯朵夫》和張承志的《北方的河》。曾騎自行車去看後者書中寫過的永定河。可以想見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氣息怎樣浸淫了一個人孤獨內省的年輕時代。
二
“到美國之後,我變得非常反叛。”在麻省理工大學讀物理學博士時,張朝陽開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
“我在銀行裏從沒有存款,買車,而且一定是敞篷車,開車路過商店時要來個急停調頭,進去買一副墨鏡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眼光閃動,飽含笑意,“我梳過Ponytail(馬尾)。那時我希望過cool的生活”。
1946年愛倫堡初到美國時已深深感慨過它的“倜儻不羈”和這種文化的感染力,人人概莫能外。
“在決定經商之前,我早已放棄了諾貝爾物理學家的夢想,他們並不是那麼受人注目的。你可能看100萬次電視才會看到一次楊振寧的面孔”,所以他在1996年時聽到華裔科學家崔琦獲諾貝爾物理獎時“沒有一絲震動”,他用手比畫了一下。儘管那是他10年的夢想。“那個社會的傳奇是另外一些人。”
“所以當時我的夢想非常crazy,想當好萊塢明星。”他看了看我的表情,指指吧臺,“布魯斯�威利斯不過是調酒師出身,對不對?我後來真的去廣告公司拍過一個廣告。還想能像邁克爾�傑克遜那樣跳舞——跳自己發明的別具一格的舞。”
三
“有一次給一位朋友打電話,我説咱們組建一支樂隊吧,他説他現在正在國內做生意呢,説你還玩樂隊?這是什麼時候了?”他轉動手中的杯子,“從那以後,我開始入世了。我看著美國社會裏華人的處境,就像漆黑的夜裏幾道手電筒發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
很多不可逆轉的選擇就要開始了,很多門會輕輕地鎖上,輕微的“咔嗒”聲要幾年後才能聽到。
1995年,張朝陽拎著兩隻箱子回到北京……1996年創建搜狐……1997年……1998年……2000年。
“回來之後沒有失望過,一分鐘也沒有,很長時間沉浸在特別興奮的狀態裏,看到遠山的景致……跟一個出租車司機報出地名……就像吃久了沒有加沙拉醬的卷心菜,忽然吃到好吃的川菜一樣有滋有味極了。那種在亞文化裏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漸被暖過來了。我慢慢地能欣賞中國人在自己的生活裏完整的熱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個人必須活在自己的文化裏才能快樂。”
但是,從西安到北京再到美國,又回到正邁向現代化的中國,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回到西安,很多親戚仍處在很遙遠的過去……生活背景的支離破碎令他有“恍惚感”。
所以我對在國內成名這件事有點麻木,可能是生活多元化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彌散化造成的——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呢?在那個群體裏的成功是成功嗎?
很多人都知道你説“誠惶誠恐才能生存”。我有些遲疑地説。
那是在商業上,必須挑戰自己,必須有危機感,但是危機感一旦緩解,虛無感就來了,像……像踢一場球,贏了,贏了又為了什麼呢?太累了,這麼多年趕路趕得太累了”他以手支頤,沉默了很久,面容在明亮光線中格外清冷。
四
36歲了,像我這樣年齡的人應該是找到為什麼而活著的時候了——為了房子、車、孩子……但我找不到依託,不知道為什麼而奮鬥。這種感覺……”他手指輕叩桌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問。
他靜默了很長時間:“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太輕了……可是托馬斯仍然為正義活著,為自由活著……”
“你沒有規則嗎?”
“沒有。接近中年的人都被上司、家人、同事種種小社會的規則穩定住了,我沒有這樣的規則穩定自己。”
我看著這個驕傲又孤獨的人,等他説下去。
“可能,必須重新發掘那些樸素和有意義的事情,或者,用理性説服自己去感動,不能這樣下去了。在週末的時候,一個人走到街上的人群裏,覺得自己像長白山上的一條狼……”
五
出租車上,他一言不發,很久才説:“按常理,談話應該是有來有往的,但一個人出了名,就可以這樣連續三個小時喋喋不休地談論自己。”他的手機響了,是記者的約訪。挂斷電話後他説:“這樣不斷地做講座,講WTO,講市場化。也許……我的生活裏其實還是有一條規則的,就是希望國家富強。”他做了個手勢,“Whatever,哪怕是為了……我自己。”文/柴靜
這場遊戲好玩嗎
柴靜
在1998年年底,如果長沙人在週五打開電視,就能看到衛視剛開播的《快樂新戰線》。加上原有的《快樂大本營》、《玫瑰之約》、《幸運99》、《真情對對碰》……這是他們在屏幕上能看到的第11個娛樂節目……一位17歲女孩説:“這一年我看的好玩的節目比以前所看的加起來還要多。”“好玩”,這個很少被討論又經常被誤解的概念,好像開始恢復一種簡單的、純粹的面貌和魅力,湖南生活頻道的導演石頭説:“我甚至在幻想怎麼能作一個好玩的春節晚會,不帶包袱純粹地玩。”
“我們真的會玩嗎?”王寶民——北京廣播學院電視文藝的研究生。他説:“學來的電視娛樂是學到了輕鬆有趣的心態還是最表面化的形式?”我們看到的只是贗品。《玫瑰之約》的製作人劉蕾談到她的節目與《非常男女》的區別時説:“我們不能打出‘速配’的遊戲口號,這個節目是交流思想的地方。”而實際上,觀眾並不這樣認為:“都是受過教育的青年人,説的都是聽來、學來的套話、漂亮話,沒有幽默感、自嘲和誠懇交流的氣氛。”製作人劉蕾並不諱言節目的弱點:“節目有50%是預先準備好的,娛樂節目那種臨場性、即時性、又可預測的戲劇性肯定要減弱一些,現場那部分的駕馭很大程度上依賴主持人。像《實話實説》那樣比較鬆弛的現場氣氛,也是努力了兩三年才達到的。”劉蕾説:“《玫瑰之約》的話題基本上都是形而上的,觀眾真正關心的敏感問題還是個‘雷區’,很難拿到電視上討論。我們做了一期節目,討論“婚外情”,觀眾發言時間最長,談的最有意思,可是我們是硬著頭皮、寫好檢討書才做的。”即使電視娛樂進入了“百無禁忌”的狀態,它也會面臨被快速複製繁殖,變得模式化的危險。《快樂新戰線》的導演樂樂説:“全國60多家電視臺來衛視取經,各種各樣的《快樂��》、《��大本營》都上馬了,哪怕是真正的快樂也會變得不太好玩,所以我們開辦了新的節目,希望給觀眾更多的選擇。”
野
“野”字就字面構成來講“田土予”,“田”田地的意思,“土”土壤、泥土、土地的意思,“予”我,給的意思。
8月3日正午,我帶著一顆驛動的心,帶上親人和朋友的祝福,踏上飛馳的列車,奔向我神往已久的海濱城市--大連!
大連是一座古老而美麗的沿海城市,她有著一百年的歷史,早在百年前,她是沙俄和日本的殖民地,至今,這裡仍然保留著日俄銀行,清晨3點鐘我們下了火車,導遊小姐劉帥迎在站前,司機郭師傅載著我們在大連市內兜風,儘管東方天空剛剛露出魚肚白,但一路上的風光可盡收眼底,清晨的大連在太陽和露水中呈現在遊人面前,我的心隨著縱橫交錯立交橋欄上的霓虹燈一起閃爍跳動,橋的右面錯落有致的排列著一棟棟二層的日式建設,這種日式民宅冬暖夏涼,紅墻綠瓦白窗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站在這裡有一種身處異國他鄉的感覺,橋的左側是新式的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橋兩側新舊建築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對比不僅是物體上的,而更深的寓意只有黃皮膚的中國人才會體會到。
大連的道路有三大特點:1、清潔,2、坡多,3、彎多,行駛在馬路上,幾乎很少能見到騎自行車的人,這是由大連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儘管沒有騎車族,但上班族一樣很便利,因為這裡的公交車特方便,即便是高峰期,也很難遇到塞車和擁護的現象。
走過北大橋,可以看到國內的跳崖,記得在電視上曾看過歌星孫悅跳崖的驚險場面,而今自己親眼目睹了跳崖景色,卻沒有勇氣一跳,真是留有一份遺憾在心頭,來到星海廣場,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那比北京天安門廣場上還要大的華表。有機會我一定要親自比較一下。説到星海公園,我們還在這裡遊歷了聖亞海洋世界,這是國內最大的一家海底世界,身處海洋世界,猶如自己真的潛入海底一般,一隻憨態可掬的海龜向我游來,揮動著龜腳與我們打招呼,這種身臨其境的感覺真的很美妙,在勞動公園,最吸引人的要數那只大足球了,大足球旁邊還有幾名球員在中聲拼搏,這一景點象徵著大連萬達球隊,由於萬達隊已解體,這裡更是人們紀念球隊的地方了。
午飯過後,我們到了海濱浴場,我那顆飄泊的心更加悸動,28年了,終於圓了我投入大海的夢,大海一望無邊,海天相接,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海,雙眼落入海灘中,眼界開闊,心情豁然開朗,展開臂膀,好想擁抱整個世界,只可惜我沒有海鷗一樣的翅膀不能自由自在的翱翔,嬉戲在海水裏,樂趣盎然,要不是導遊小姐催促,我真的不想離開。
當我們再次返回大連,讓我用似曾相識的眼光重新接受這座城市,馬路上那特有的有軌電車勾起我童年的回憶,與大馬路上行駛的雙巴和進口轎車形成鮮明的對照,而正是這古老的有軌車儼然成了一道活動著的亮麗風景線,寬闊的人民廣場,喻言著大連人好客的品格,站前勝利廣場的購物環境格調高雅,置身其中很是愜意。
晚飯後,給媽媽通了個電話,電話裏媽媽的聲音似乎很緊張,在她眼裏,平日怕貓怕狗的我一定會想家,當媽媽聽到我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時送了我一個字“野”。身處異鄉,卻絲毫沒有念家的感覺,難道我真的“野”了嗎?不,不是,祖國山河地大物博,生活在黃皮膚、黑眼睛、黑頭髮的群體中,天涯海角處處都是家。
如果現在問我最想做的是什麼,我會脫口而出,帶上家人一起遊歷大江南北,如果有機會我還會重走大連,插上翅膀,盡情遨遊,放飛心情,永不駐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