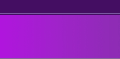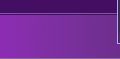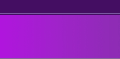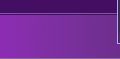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
| 用我一輩子去忘記 (五) |
北京秋天,陽光很好,天藍 ,風大。走到陰影裏的時候象被水浸了一下。
在報到的地方我和一個叫琛子的女孩排在一起。她也是湖南人。我們考分一樣,分在一間。都穿黑衣白褲。只是她的頭髮是亞麻色。
一起尋到那間叫634的小房子,上下鋪的小鐵床,一張老褐色的木桌。一個穿牛仔裙,極短髮的女生抬起頭,濃眉重睫,笑容狡黠“我已經拖了六遍地了。”她是株洲電臺的主持人張宇。也做夜話節目。
人生奇詭,處處與舊日生活撞在一起。
加上山東的小美,林林,五個年青女人陸續住齊,安頓好行李躺在床上,人手一本日記伏在膝蓋上寫。咦,到這個城市來的人,心事都這樣重嗎?
我背靠鬆軟的枕頭,插住耳塞,齊豫唱“迷人的是忠誠還是背叛。幸福是自由還是牽絆?”我想想,寫下答案“迷惑極了”。
遠遠地,遠遠,是鮑家街43號在<晚安北京>裏唱的“國産壓路機的聲響”,不絕如縷。
第二日起五人連袂坐在教室第一排,吃東西,喝茶,看片子,聽張宇接老師的下荏。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起初有認識不認識的聽眾來找,我裹著棉袍,無可無不可地聽著。
都會過去的,看孟京輝的話劇裏説“ 風一樣聚攏又雲一樣跑開,雪一樣凝固又水一樣流去。”
震蕩久久不能平復。
拎著小紅桶去洗澡的路上,天地象水洗過一樣的清澈明凈,風潛入赤著的腳踝。粗糙的石子路,濺開著的淡黃雛菊,處處使時光倒流。。。。。彼時我是無名少年,充滿不可解的悵惘。而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唉。氣候的乾燥使臉部和頭髮變得粗糙。每天11點就寢,7點起床,使人視吃飯為較有刺激的事。人變得懶於思考,勤於長胖。我隨身行李中只帶一本<紅樓夢>,睡前翻幾頁。從不看後四十回。也不全是高鶚的原因。前半部的書裏有一種氣氛,是我貪戀的,象爛漫喜笑的童年。
偶爾熬通宵,五個人喝杜松子酒,吃閒食,打牌,最後只是聊天,愛,性,少年歲月……林林總總的真心話。我們精神飽滿至淩晨,喝完豆漿上課去,個個青面獠牙似奇異鬼魅。
我們在宿舍齊聲念西蒙波娃的句子“我厭倦了貞潔又鬱悶的日子,又沒有勇氣過墮落的生活。”
沒有自己的房間,電視,熱水,爐火,沒有關係親密的人,只有女人幾名互勉。
但星寶給我信裏寫“女人和女人,越親密,越覺悲涼,然而與男人呢——大多象偎著微溫的小火取暖”我回信裏要她重新留起及腰的長卷髮,在春天裏露出白楊樹榦一樣筆直的腿,“象一面旗幟一樣在風裏走。"
龍一的E-MAIL裏説“如果不是因為情慾或是極想要孩子,我不覺得有男人的必要。”我嘆口氣,復信給她,要她離開乏味的新加坡,去一個有瑪格麗特。杜拉筆下“藍眼黑髮”的熱烈情人的國度。
諸人都以為靈魂是唯一的財富,儲蓄等待升值.
但進入一個陌生城市的女人,遇到的,不過是男人們用狎昵的口氣説“你挺漂亮的,不愁出路。”這句話,這讓人有微微的厭惡與悲哀。明白一個女人憑藉靈魂而被愛,只有在廣播中才有可能。
電臺里正放王菲的老歌《誓言》“如果你能給我一個真誠的絕對,無所謂,我什麼都無所謂”,那是多久前的誓言?此時滿世界正炒作她是如何被背叛的。愛情是女人的信仰,只是教主太脆弱。
“那麼,”琛子問我“什麼是真正的愛情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什麼不是。
我低頭翻過一頁書。
陳丹燕正寫到在慕尼黑冬夜街頭看到鬱金香開放,她伸出手觸摸花瓣,“是真的”她輕聲對自己説,快要哭出來了。
我在日記裏記下這一剎那,“對於美和愛情,我一再被表象和幻覺所蒙蔽,沒有觸摸到它的根須,雙目所見,雙耳所聞,都不能讓我信任。我要在巨大的黑暗中,靠我的雙手最敏感的指尖觸摸它,哪怕是在生命的盡頭。”
夜夜記完日記,聽大佑的情歌入眠,在起伏升落的悵惘中沉沉睡去。最愛那首<思念>"蕭瑟的風雨中,你走在我身旁,陪我穿過那深深黑夜微微的光," 呵,在黝黑深邃的空間裏,這歌蒼茫溫柔,致人于死地。
到下半年,大家漸漸有社交活動,週末只有我和小美在。
我們夜夜看小説到淩晨。睡前拿三大瓶熱水泡腳。
“是人生最大享受,嘎?”
她點頭。
“也沒有人説,來,帶你出去玩。”我迷迷糊糊睡著前,聽到她惆悵地自言自語。
第二天寒雨擾人,去吃了一碗熱面暖身子,想起沈從文站在北京暮色中的城樓上,“覺得生命著實的孤單”。
這虛無之城。
我願有信仰,憑藉狂熱的祁禱與純潔的獻身精神得到依託。這樣在人世中我不必毫無依恃。在最哀慟時可以匍匐于神足下,可以將我與最愛的人們的幸福託付給宗教,我們將得到庇護。
我仍如年幼時夜夜向不知名的神發問“有沒有一個人或一件事有這樣神奇的魔力,使世界從毫無意義的桎梏中解赦出來?”
無人回答。
只得喃喃念誦普希金的詩句“在西伯利亞的礦坑深處,請將高傲的忍耐置於心中。”
課堂上放平克弗洛依德的錄影帶,那陰鬱的<迷墻>,狂熱的,幾乎是患病的人才會有的敏感和絕望,令聽的人靈魂戰栗如一顆水珠。
下了課,曖氣片附近都站滿人,擠擠挨挨地取曖,照例誰也不看誰,也不説話。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
在下午的天光裏看李氏姐妹的<沉雪>,看到在冰冷的北大荒的寒夜裏,舒迪為孫小嬰撫摸脊背,那細緻的溫存“戰勝了空虛,孤獨和疼痛”, 我合上書,站起身。 暗藍的暮色象海水一樣淹沒了道路,我茫然四顧,不知道自己是誰,身處何方。
夢中看到幼時的我,一點點大,站在墻角看別人作遊戲,我慢慢蹲下身,向她伸出手,她含著姆指,大眼望住我,卻只是笑。
第二天我在去上課的路上,停下腳想了想,轉了個彎子去車站,買了最快的一趟回家的票。
少年時的荒草與舊樓已消失殆盡。倒是幼時的故居,處處荒煙鎖閉。滿屋的陳年舊事和被光照亮的塵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