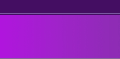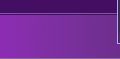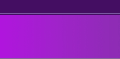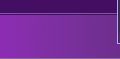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
| 用我一輩子去忘記 (四) |
第一次節目沒有任何預告,在花鼓戲後面就開始了。還開熱線,用40分鐘談張愛玲。居然爆滿。
可見似錦繁華的夜,處處有寂寞的信徒。
之後的三年,我的週末都在電臺。晚上十點半的節目,下午兩點去,和整幢空樓廝守,對著滿桌子的信,音樂。下午的太陽照進來,地老天荒的昏黃。
窗口正對著老榆樹,倦了便望望它,春綠冬白,永遠永遠。
然後,夜慢慢慢慢地來了。我坐在調音臺前,熱線開始之前一小時已有電話在等,兩盞小綠燈閃爍不寧,象一個人內心欲言又止又呼之欲出的話。
時間象只咻咻的野獸在身後趕,面容與聲音都會老,我有一天會無法再穿貼身的長裙,纏到腳踝的高跟鞋,無法再有散落在肩膊的細軟黑髮。 於是愈發在節目裏極力用聲音留住這一瞬,才不會在無涯的時間裏化為粉塵。
在節目裏,從不相識的人那裏獲得無數知已之感。端著裝滿信和音樂的籃子下樓,在黑暗裏想“可以死而無憾,"
但還有一件事。 滿櫃子的唱片磁帶,鄭智化的也很有幾張,但那首歌,卻遍尋不著,不過日長天久,就死了心。
我開始穿彩衣,下意識彌補少年時代,深紫淺紅煙藍竹青,卻沒有用武之地,只每日在臺裏廝磨時光,與同事聊至爛熟,圍著火爐將七情六欲,嬉笑怒罵一一上演。沒有他們無法度日。
男男女女都年紀相若,沒有家室。下班了在星寶的斗室裏混飯吃,她一邊尖叫著説煩一邊挽起長髮給我們炒紅椒肚絲。我們都愛她。
宋揚是我的心腹,他頭與身子都滾圓,在辦公室穿老虎頭拖鞋,跟馬路上的小雞小狗彎著兩隻胖指頭説“嗨”。我們每天一起吃飯,算清每一分錢。如果是他請我喝礦泉水,就一定要求我買一支冰棒返他。
臺裏出去搞活動,領導唱象古老石山的<十五的月亮>,他都領頭把燈關掉,用打火機閃,還要大家手拉手造波浪。領導羞澀又開心。
笑得我。
然後大家裝體力不支昏睡,可以早早散場。一幫人呼嘯一聲,去自己的地盤玩。
樂樂是我們的老大,大眼雪膚,清新闊朗。她帶我們在的廳裏玩老鷹捉小雞。 楊景和我假模廝樣地深情對唱《請跟我來》,諸人紛紛作被電到狀。散場後的淩晨,天色是詭異的紫,人人在那樣的寒冷裏凍得咯嘣脆,我們把附近的小店子的門拍開,要餃子吃,何晶講無數葷段子,睡眼惺松的店主蹲在火邊,也跟著笑,滿懷的火光。
或者是,沉的夜,下著瀟瀟的雨,幾個人買了煙花,在街上行人裏放,在夜雨中炸開的煙火與脆響,讓人明白此情可待成追憶---於是更加放肆.
一切都在節目裏説給人家聽,年紀小,不怕肉麻。結尾説到感動處,還説“蓋好被子,乖。”
第二天不敢進辦公室,還是沒躲過去那些人的爆笑。
我實在愛長沙這個城市,愛它無常的天氣,毒辣的太陽,入骨的濕冷,連月曖昧不明的天色……愛它無辣不歡的飲食,嘈雜市儈的男女。
夢裏不知身是客。
只有一年一次回家時,在荒蕪的北方大地上行走,在春天的泥土裏留下的腳印,在剛剛剝開的綠色豆莢或用手搓開的碎金一樣的玉米粒中聞到的氣味,提醒我的來處。
一家人靠在沙發上説説家常,妹妹的身高已略略超過我,我對她的了解止于幼時記憶,我們仍偶爾吵嘴,和睦時便一起在鏡前試用各色胭脂水粉。在小青家,高蓉讓我將手放在她腹上感覺胎兒的心跳,我們一直交握著手。等到收到她寄來照片時,小妞妞已半歲,可愛之極,如同天使,淡藍眼眸,嫩紅嘴唇,長大一定美麗到讓人心碎。我盯視這憑空而來的嬰兒,不明白我的少女時代去往了哪。
難以左右的世事還多,樂樂去《快樂大本營》,星寶去經視。洪亮去武漢,辦公室一時蕭條。那時範波還在,每日被功名心煎熬,裝病去做生意或是準備考研,偶爾打電話來探風聲,遇到是我接,他就長嘆一聲“噫,柴寶你説得對,真是朝如青絲暮成雪。”
我記得清楚,4月5號做夜色溫柔,主題是“依靠”,寫開場白時幾次心酸悵惘,“從來到這異地城市起,我便鐵了心依靠自己,我們都對生活認真,知道什麼是同事,什麼是朋友。但在這時刻,我恨不能忘情下淚……”
任賢齊唱出“我讓你依靠,讓你靠……”我心酸眼熱。
背景音樂,是劉星的<一意孤行>,直到它被到處放濫了也在用。那支曲子叫《閒雲野鶴》,原應無比舒展,卻是蒼涼的,伴我兩年時光,封面那身影在林莽雪原中獨行,是自由,也是孤單。”
靠得住的憑據,只是這一隻話筒與“人間世”中燈火簇亮的一瞬。
説到底,人跟人,沒有什麼不同,尤其是寂寞的人。日子長了,聽節目的人都在信裏説“把你當另一個自己。”
下了節目十二點,外面是大月亮或是鵝毛大雪,時不時會有三兩個人等我,在離開這座城市前來道別,陪我走一段,揮一下手説再見。在異地也寫信來。不説什麼,只在信末要我為他放一首歌“如果想要得到一點溫柔都是奢求,是不是所有的臉孔都該停止笑容。”或是在香港,北京,天津。。。。。深夜的街頭,打來電話説心事,這麼大的世界,能信任的只是一隻小小無線電裏的聲音。我在電話彼端,不知心酸還是安慰。
推不過時也去大學和聽眾見面。幾次都是人太多,桌椅也擠壞掉。我被押送到學校保衛科,人群久久不去,齊聲大叫“柴靜”,真戲劇化。我不能理解,只覺尷尬。
有更營造氣氛的地方,大家點了蠟燭,齊唱“讓我擁抱你入夢”,令臺上的我難為情。但很多人聽節目是為這首歌,我明白。
也有感動時,偶然説喜歡簡單的黃菊。過一會一個男生走上來,遞給我一支,什麼也不説。花瓣與頭髮上俱是細碎的雨珠。
回去把收到的花散一地,用水晶瓶,大肚陶,重新插好,丟一粒維C在水裏,要開很久才衰。
花香令人恍惚。真切的,只是床頭微紅的燈,厚軟的被枕,幾本書,和絕對無人打擾的安靜。含一顆梅子,微酸的核鼓在腮幫子裏數小時。
一剎那覺得,就這樣停留下來吧。在這如同流沙幻影的世界上,夜深如海時,為了那些悲歡翻捲的心,讓我來守著這一點點恒定不變的東西吧。
然而夢裏仍是十四五歲,站在不停休的大雨面前,看玻璃窗上水痕斑駁,我看不清她的臉,不明白她在凝視的是什麼。
夢真重,象沾滿了那些年的雨滴。
98年,發給我的名片上寫著綜藝部副主任。節目有了穩定的廣告,報紙上有了自己的專欄。常常有電視臺的邀請。
決定去讀書,不為什麼,直覺應如此,其他理由都是遁辭。同事中只有宋揚知道併為我謀劃。惶惑時便問他對不對,他一疊聲説“對對對_發跡後別忘提攜我先。”
臨走前同事們終於知道了,情緒熱烈。“北京的男性環境比湖南好。”女生説 。
“沒關係,你走了我來作夜色溫柔,”楊景笑咪咪。
看,都毫無離愁。
宋揚學著我節目裏的腔調怪叫“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我笑罵他。
這人從不聽我節目,只有臨走前某晚他拿薛岳演唱會的錄音帶要我在節目裏放,他為我倒好帶子,放給我聽“如果還有明天,你想怎樣裝扮你的臉,如果沒有明天,要怎麼説再見”,我看到他臉上一閃而過的悲哀神色。
當晚的最後一個電話是個平常的湘潭女孩打來的,她説她知道她生了病,瞞著父母去醫院做了一個簡單的檢查,沒查出什麼——可是也許是比想象更嚴重的病。她不想知道。打算明年七月高考結束後再面對真相。“到時候總算有你在。”。她説了一句平常的話,可就是這句話讓我在節目裏掉了眼淚——沒有明年的七月了,沒有這樣親如骨肉的信賴了。我緊閉著雙眼不肯面對的,它就要來到了。而時辰一旦逝去,一切永不再來。
下了節目,隔壁經濟臺的阿袁等我,她沉默地走在我身邊,她懂得。我狼狽地走在夜裏,流著眼淚,不知向哪呼喊,呼喊在子夜時的我自己飽滿的心靈,呼喊微雨中青濕的馬路,呼喊清晨盈耳的鳥叫和乾淨的清水,呼喊被愛著的我自己。
長沙,長沙,我曾沉溺于這個城市,我聽過這個城市不休的嘈雜,連綿不絕的哀傷和大地沉沉的鼻息。在這裡,我貪婪吸取那青綠山水之間的潤澤,貪婪地吸取屬於一個年輕女人的美和愛,永無魘足。
很久之後我從小燕那裏知道,星寶在那一晚給她打電話。哭泣良久。
她看了看我的表情,説“你一直不知道很多同事聽你的節目嗎?”
最後一次節目時,悲傷已經過去了。我只記得熱線中,那人不驚詫,不挽留,只説:從此後只能從酒精中獲得安慰。
兩年後在北京遇見蔡琴,告訴她我曾是她的聽眾,後來也做一名主持人,再後來,離開時,播放的是她的<渡口>“讓我與你握別,再輕輕抽出我的手,知道思念從此生根,華年就此停頓。。。”
我的心如錚錚琴弦撥動。
火車開動時,手覆在玻璃窗上向外看,這裡的小湖……綠……荷花……雲,真讓人繾綣。我曾妒羨那些築居於側的人,一輩子,就這樣悠悠地過去了,小城中,小小的悲歡。呀。
沒有忽然而來的清風,沒有高而藍的天,秋天就這樣在纏綿的雨裏開始。我辭職去往北京——帶著北京廣播學院的通知書,剛夠用的金錢,面目不清的未來和22歲的年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