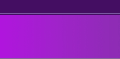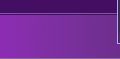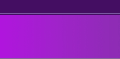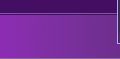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
| 用我一輩子去忘記 (三) |
我考上南方一所二流大學,在那裏學會談戀愛,跳搖擺舞,靠寫文章出盡風頭和賺到生活費。去唱歌時,我試著找過那一首,從來沒有。只有一首接一首的粵語歌。
跟小男生在南方濕潤的夜霧裏牽著手走,他低低唱李國祥的“摘下星子千串,挂于你窗前。”墻側有桅子花香暗暗傳來,不是不快樂的。
只有在大風的夜裏,過長廊去洗手間,風從窗洞裏呼嘯而來,人怔忡不安地站在淩晨四點奇異的青紫天空下。一點關於北方的記憶,在那首歌裏翻來滾去。
週末去跳舞前在宿舍裏大家一邊化粧,一邊聽收音機裏洪濤的排行榜,他的聲音溫和雅正。散場回來趕上尚能的談心節目的片頭: “遼遠之中,夜渡心河”,全體女生被他的老練辛辣吸引。我們都在日記裏記下那些電臺裏的故事,我在94年10月22日那晚記著,一個女孩為愛情沉鬱頹唐,尚能説這個人只是一種不願脫離的習慣罷了,他説請給自己“一點勇氣”。
三年後他自殺,據説是為了愛一個人。 我聽到他最後一次的廣播,只記得他説“王平是一個有大智慧的女人”——王平曾與他一起主持過《夜渡心河》,知性與慧心兼具的女性。
又過三年後,我幫王平的《音樂不斷》的歌友會做一次“救場”的主持人,散場後我們去吃宵夜,她説她也聽到了那次節目,她轉動手中裝滿鮮橙的杯子“去電視臺的原因是尚能的死給我觸動太大了。””我們都不相信他的死只是因為一個女人。
也許是我們都不願相信人是多麼簡單脆弱。
我對她講起我當年是女學生時寫信給尚能,希望做電臺主持人,信寫得極天真“尚能也曾有夢,可否幫我成就夢想?”
我一直以為是這句打動他。因為他後來幫我做到的,恰恰是我的夢想,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
我第一次節目是在學校廣播臺裏錄完的,7月份,錄音間沒有空調,錄完後整個人濕淋淋,令同學駭笑。我拿去給尚能聽,他聽完我第一段説聖克裏斯朵夫渡人過河的故事,Beyond的《海闊天空》響起時,便按下鍵。他背對我,看不清他的表情,然後他轉過身來説“今晚播。”
我騎單車20分鐘回住處,鎖好車,蹬蹬蹬跑上六樓,看著自己在車把上磨破的手掌,十分十分地快樂,當晚的日記裏寫“有風吹過,生命新鮮清香。”
那個節目叫《另一種聲音》,在他的節目裏原來放睡前音樂的時間,子夜前的最後半個小時,有聽眾為我保存94年第一期的錄音帶,今天再聽,極其原始粗糙。但那當中……有什麼呢?在那個少女淺白清冷的聲音背後。
我與尚能並沒有因為節目的聯絡變得更熟稔,經常是,我去辦公室時,沒開燈,頭頂風扇嗚嗚作響,尚能背著我,不説什麼話,等他先去樓上直播間了,我坐在他桌前整理稿子,滿桌是灰白的煙灰。我那時覺得他很容易陷入頹喪和沉默。
但我正沉浸于發現自己的興奮中,簡直無暇顧及他人。直到他在華年離開時,我也未曾與他有過真正意義上的交談.
電臺是份奇怪的職業,大家在節目中那樣推心置腹,彼此見了面反而是哈哈哈。
我每個午夜帶大疊稿子和磁帶去做節目,那樣的夜,有一種魅惑之感,人好象可以不沾染 塵埃。我在節目裏也感染這氣氛,覺得心安靜下來的時候,塵世裏的一切聲音都聽得到——一滴水和另一滴水相遇的聲音,青草長起來的脆響,叮咚作響的雪片…… 。
這些聰明和敏感本來是女學生式的,但這份工作讓一個女性有充裕的時間和足夠的機會培養分寸感。控制自己的情感,增添一些內省的氣質。今天回過頭再看這份工作之於一個人的意義,感慨擊心。
在電臺的資料櫃子裏找到很多好聽的歌,還是沒有那一首,只有另一支鄭智化的,叫做《讓我擁抱你入夢》,我覺得那句“玩火的孩子燙傷了手,讓我緊握你的小拳頭,愛哭的孩子不要難過,讓我陪著你淚流”,在夜深的時候聽,是有一點悲傷的。
然而卻是,那麼那麼溫柔。
十九歲那年我開始做《夜色溫柔》的時候,這首歌是我的片尾曲。我急著打電話給高蓉,卻忘記告訴她。只為聽到她和冬冬要結婚的消息開心。
而彼時的我剛剛大學畢業,拒絕做一名小會計,自作主張遷了戶口和工作關係,租來城市邊緣的兩室一廳,空落落的房子,我在地板上扔幾隻大墊子,隨坐隨臥。陶瓶裏幾枝野地裏撿來的荊棘,蒼黃老綠.靠積蓄買到一台CD機與可喝紅茶的水晶杯,開始我的職業生涯。
開始的日子最難捱,在陌生之城,聽不懂方言,沒有錢,沒有朋友,於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又是青春期最難看的時候。十九歲生日那天身無分文在滂沱大雨中走到電臺去,在節目中説 “要做一隻翩飛的白鶴,飛渡寒苦的人生”
也只有那個年紀説這樣的話才不會惹人笑。青春本身自有尊嚴。
南方秋季亦多天風海雨,坐在屋內,也能覺得迫人而來,長夜裏人的情緒完全不能自控,看一篇普通童話的結尾説“以後的日子天天快樂,夜夜平安”,也要倉惶下淚。
於是夜夜守住電臺節目,貪戀那一點人氣的溫暖。且當中有無數詭異故事,人人依恃聲音隱沒身形,可傾吐最隱秘之心事。有一晚停電, 漆黑裏聽新加坡電臺林偉的《點一盞心燈》,他要言不煩,“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燃燈火”
是。遂決定作午夜的節目。
電臺在週末的夜是放4個小時的花鼓戲。我請纓做一檔直播節目,主動要不計工資,苦心積慮地遊説領導,“可以省下一個放磁帶的人工呀對不對,”終於被同意,想了幾個名字,都太刻意。臺長隨筆改了《夜色溫柔》,正好是菲茨傑拉德的小説名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