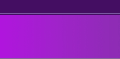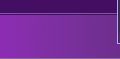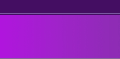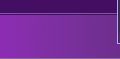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
| 《方興東:孤獨是一個人的骨頭》 |
第一次見方興東,是在上海。
《新青年》錄一期節目,評十大新銳人物。張元,司馬南.....各色人等,被安排種種名目登場。方的名頭是“最具挑戰精神”,因為人人都知他跟微軟打筆仗的事。錄完節目的當夜,大家呼嘯一聲都散了,只有他和李陽留在酒店。閒極無聊,李陽組織去外灘。一路上,上海的聲光色影在車裏掠過。人語喧嘩。方也不大説話,只微微笑,象一個脾氣好的小孩子,跟著大家在江邊亂走。他問我聽什麼音樂,我摘下耳機給他聽江天的《上海夢》,他聽了一會,也不見得有什麼感慨。
所以後來看到他的詩很驚訝,是很敏感的人才會寫出的那種,他寫鳥,父親和土地,女人,瓦藍的藍,被捲起的樹蔭和大朵大朵砸下來的雲。 一顆一顆的字,潔凈之極,水墨的風格。有天清早上街的時候,想起他的句子;天已亮了/行人紛紛黑下去。就跟他約了採訪。
他的辦公室在清華附近的學聯大廈,玻璃隔開的小房間,有一種粗糙的蔟新。筆記本電腦,文件,他的書,全是計算機方面的。小沙發,小幾子,人來人往,都顧不得坐。
他一邊招呼我,一邊放下電話,説是南嫫打來的,“八幾年在西安的時候一起寫詩的,包括伊沙。”他倒了杯水給我,“那時候寫詩是一件很時髦的事,象今天的互聯網一樣。”
他穿淺藍襯衣。有一張清秀而微含憂戚的,但難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臉,拿杯子的手很柔軟。
“現在?現在已經不寫了。有了互聯網就不太可能寫詩,詩是要孤獨感的。這個行業.....整天無數的事情,那麼熱鬧,根本靜不下心來寫詩。”
他是訥于言的,很少直視女性的視線,急起來有些口吃,但一説到互聯網卻神色自若,看得出他的愉快興奮,“互聯網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受益最大的是65年到75年出生的人,這天生就是為我們準備的——就是我們這幫沒有錢的年青人。”
“這就是理想生活。” 他很享受自己朝九晚九,沒有週末的工作。
“現在偶然看到夕陽,天空還會不會有詩意的感覺?”我笨拙地引導他。
“好象沒有。”他回答得非常流利。
“嗯——靠想象力在生活嗎?”
“沒有,想象力也不多了吧。”
“天哪 。”我實在忍不住笑。
這個人,他還在説,“有想象力也不是詩意的想象力,是想互聯網的走向。這個行業的人都是很單調的,如果你已經有條件過得很舒適的話,你肯定不可能這樣拼命地往前衝了。”
我驚訝的只是他毫無內心的分裂感,96年他從西安來北京讀高電壓博士時,寫了十年的詩,帶了兩千多冊,12個紙箱,從口糧裏節省下來的文學類的書。8月份,因為電腦公司的同學説“可以增加點收入”,開始寫計算機方面的文章,在這以前他對這個行業從無了解,也從不感興趣,但從那時候起,“整個人的精神狀態就不一樣了。”97年以獨立撰稿人身份寫稿。99年批判微軟“維納斯計劃”的文章出來,影響力達到業外。去年九月停學辦公司。
在樸素的功利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他居然毫無搖擺。
“我這個人,在文字中是很理想,很浪漫的。但在現實生活裏表現得非常現實。象我喝酒,可以喝到十幾瓶啤酒,但從未醉過,我知道那個極限,到那裏就決不會再喝。”
他並非為自己而生活——他不是投機分子和利已主義者,但他知道什麼是肥料,農藥,和破舊的房子。“這是真實的生活/勞作的人總是疲憊/生著病/咳著血。”對他來説,貧窮一直是懸于頭頂的沉重死板的巨石。
“我爸爸非常喜歡喝酒,我上高中時最大的理想就是一定要找一個比較好的工作,每天買酒給他喝。結果等到我畢業的時候,我爸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喝酒了。”他説起父親總是有一點悲哀的神色。
他的一首詩寫生病的父親,格外沉鬱頓挫,結尾説“大街上/田野上/誰需要一個貧窮的父親/誰需要一個傷心的兒子”。
父親近年沉迷賭博,他也不好勸,只有説:“你身體不好,呆一會兒就回來吧。”
他是長子,對父親一直有這種奇異的了解與悲憫。
直到上研究生,他都在放假前一兩個月鍛鍊身體,為了回家幹農活。“累,在三十五六度的天氣下,汗也非常多……但非常好。”
我看看筆記本上記的他在89年的詩,“比我們更高更大的作物們/紛紛匍匐下來/我們彎腰/默默除草/讓四面八方的波動告訴遠方的人/種子的由來就是/我們的由來。”
我們進了路邊的小館子,他要了幾個炒菜和酒,給我要了一份奇形怪狀的拔絲蘋果。周圍是尖叫的小孩子和為股票爭吵的男人。
“中國人在骨子裏是很有饑餓感的。隨時需要爭生存空間,再有錢,骨子裏還是個貧民。——這樣也是好的,象美國那樣一個‘非磨擦’的社會,人多麼寂寞。”方興東説。
我想起有人説他的文章“快意恩仇”。
“特別是微軟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啊,他們動用了四個公關公司,從各種角度要怎麼著,壓力特別大,但是狀態特別好,每天都是要跟人打架似的。這樣無所顧忌,”他雙眼閃亮,興奮感久久難去。“互聯網是一支爆竹,它在透支你的生命,你現在還年青,興奮,身體又比較好,感覺不到。但不管將來怎麼樣也不會後悔,再沒有這樣的機會讓你這樣折騰了,”他頓了頓,笑了,口氣揶揄。“哪一天落魄了,正好去寫詩。”
鄰桌幾個剛進來的年青人忽然探過頭,“方興東吧你是?”問他辦網站的事,約好第二天去他辦公室談。
“中國沒有互聯網,精神狀態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他語風簡斷,“上個月去美國,在MIT,很多人對張朝陽不服氣,我説‘那你們去試試看,’互聯網讓一些沒有錢,沒有勢的年輕人,在合適的時候,站在合適的地方。還應該有更多的人站在這個位置。互聯網的變革力量讓他們的心態、價值觀要比過去的人好的多。——用不用互聯網倒沒有多大的意義。”
我不習慣一個這麼有生活興奮感的詩人。打斷他:“老了以後呢?” “一定回農村去吧。我身上詩人的這一部分可能是對過去的迷戀,小時候的春天特別美,那時候上學坐不起公共汽車,一路走回去,真是美。去年回去專門走了一趟。非常累……村裏的每一個人一想起來,他這麼多年的經歷都能想起來。任何地方,十年,二十年前,這裡長著什麼樣的草,我都知道。一下雨,我就知道哪兒會有魚。”
“小時候, 在村裏,一個人。很孤獨。夜裏,常去小山坡上坐著……”
他聲音輕到我聽不清。
“現在我很難忍受一個人生活。我曾經非常內向,很自卑,那時候真孤獨。高中時的日記裏寫‘上帝為什麼要讓我長這麼高?’你覺得可笑是嗎?但是當時讓我苦惱之極。直到中學畢業,從不和女生説話。”他解釋性地抬頭看看我,我點點頭。他的詩裏寫過“多麼苦呀/沒有愛人的歲月”。
但彼時他已是知慕少艾的年紀,看《平凡的世界》看到骨子裏,到西安唸書時他專門去問路遙“為什麼要讓田死?是因為你不知道該怎麼寫下去了。”路遙沉默了一會説:“你就這麼想吧。”
他欣賞的女性是哈代《遠離塵囂》那個女主角,《飄》裏頭的郝思嘉。——“挺有個性,挺堅強的。”
“大學裏東北一個女孩,88年一個晚上,我們一起跳舞……可是,要我去表達,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後來89年戀愛,寫信是生活中非常好的一部分,情書……一天兩三封。四年。我提出分手。那是我一生中唯一對不起別人的事。”他耿耿於懷,“那時年輕,以為將來還長,還有很多……現在?……我有個最佩服的朋友,87年到現在,一直在苦苦地愛一個人,我跟他説,愛情,這東西,你要認為它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他對自己的話肯定地點點頭。“和諧地生活在一起是最重要的。”
孤獨,在一個人的生活裏被成功地,乾淨利落地撥除了。我打量這個人,再讓他接近詩,除非是很大的命運性的力量,或是,很久很久的時間吧。
可是。
“孤獨……,”我們站在同方大廈前等車時,黯淡的夜裏,他對著一街的燈火,沉默了一會,卻讓我意料不到地説:“也許,還是有吧。”
車就來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打開他的書,第17頁寫著“抽掉孤獨如同抽掉一個人的骨頭/而生活就是幹活/幹活就是一種投入/就是要無限地重復一個動作/使一切不易斷裂/我必須忍住/一種呼吸和哆嗦/必須把勞累和緊張平息在尺寸紙間。”想起他在 結完帳出門時突兀地説了一句,“詩不能成就我,但讓我發現我自己。”
是的,他是知道的,他早已知道。
(方興東,31歲,清華大學博士,IT業著名評論家,“數字論壇”成員,中國信息化産業專家論壇主要學者,主要著作《起來——挑戰微軟“霸權”》、《騷動與喧嘩——IT業隨筆》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