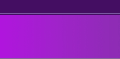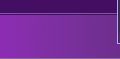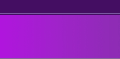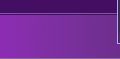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
| 丁薇:我的音樂比我更放肆 |
看見丁薇會知道,那些鏡頭上、照片上的彩色織錦,金鎖片,墜滿流蘇的頭髮,都不是她。
她,穿牛仔褲,深灰毛衣,平跟鞋,容色清楚。
坐定後,要一杯咖啡,“熱熱的。”
喝咖啡時,貪婪地喝一口,大眼瞇起來,差點“唔”一聲表示享受。
她和一切生於70年代的女孩子沒有兩樣———
7歲時因為爸爸有個同事“會點兒二胡”,加上“能買得起”,開始音樂生涯;12歲時的夢想是不想做一個平庸的人,不想朝九晚五地生活;16歲時聽蘇芮和齊豫,喜愛唱歌,但從沒有被人讚美;20歲時,她是上海音樂學院作曲係大三的女生,心事青澀。
“遇到感情上的挫傷,坐在鋼琴邊上,隨手彈出來。叫做《猜》。”
那年暑假幾個朋友要跟大地唱片公司談簽約的事,“跟着去玩玩吧。”於是一起坐火車到北京,住在地下室。
去公司時她站在人群後面,大家都談完了。她輕咳一聲:“我也有一首,要聽一下嗎?”
三寶聽的時候一直低着頭,看不清他的表情,然後他抬起臉問:“你要不要轉學到北京來?”
過了一個月,公司到上海來找她簽約。
很快出第一張專輯,叫《斷翅的蝴蝶》。那是1995年,樂評人難得見這樣清新的女孩子,“又有一點藍調,另類”。眾口一詞地説好,但緊接着是銷售上的失敗。
她決定停下來,只給別人寫歌。《女孩與四重奏》的第一個版本,寫給馬格,公司的企宣。一個“挺噶”的“長得不好看”的戴眼鏡的姑娘。
5年過去了。
“我等得太久了/等得心也灰了,我想得太久了/想得人也累了”今天她再出新專輯,重填再唱這首同名的歌時,竟然紅得不得了。只是,歌詞中已經滿是時光的痕跡。
“我在學習。”她遞給我那張叫做《丁薇&開始》的唱片,封面是她在行走。兩側是磚墻,塑料,鐵欄……粗糙堅硬的世界。她不言不笑,光從四面八方來,照在她臉上。
當年大學畢業後,來到北京,在這個“可以窮,可以普通地活着的城市”,四處搬家,幾乎沒有工作。但作曲係的經驗可以幫助一個人一天寫十首歌來謀生。
她的歌大多有冥想的氣息。很女性,但毫無脂粉氣。所以這自省的女子,歌中充滿如蛭附骨的孤獨與疏離感。“開始/懷疑自己……開始/嘲笑自己的扭曲。”
那樣涼的歌詞。幾乎碰不到精神的熱度。可是,音樂卻帶着兵氣,用低鳴的弦樂編排和強勁的House節拍交合來襯出異樣的絕望與狂亂,甚至妖異。
“在音樂上我比我的人更放肆,更張揚。”她用指尖蘸一點藍染在眼角,睫毛的陰影蓋下來,像只小手掌。“我真正喜歡的生活……是很懶散的。在百無聊賴中看看書,寫寫東西,然後90%的生命給音樂。”
朋友也都是幕後的音樂人,金武林,劉效松……大家聊天,吵架,吃飯,做音樂,把每個人的東西,一點一點加進來。
“結果像化學反應一樣奇妙,每一步都知道是自己做的,可是最後那一瞬間,都怔住了————是嗎,這是我們創造的嗎?怎麼會鬼使神差地變成這樣了呢?”
我問她這些年在她身上最大的變化。
“在音樂上更自信,更主動。”她什麼都做,寫歌,編曲,製作助理,包括錢怎麼報銷和分配。
“我明白了什麼是流行音樂,明白了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歌手。”
她要做Rickie Lee Jones和比約克,不見得有年度獎和唱片銷量,只是一直存在下去,“無可替代,無法劃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