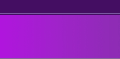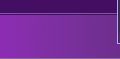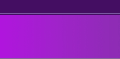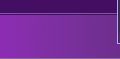|
| 遇見蔡琴 |
我聽蔡琴的電臺節目比聽她的歌早,大約十年前。
那是台灣中廣流行網的“日正當中”,她主持了十三年,最後一期,卻不動聲色離開。等到可以問她原因時,是在多年以後的北京。7月21日晚上,我們對坐,中間隔了走來走去的人,燈,還有時間。
“因為那時候離婚,心情很不好。電臺非常反映我的真實性格和內心生活,那是一個幽默坦白的節目,以那時的心情是完全沒有辦法做下去的,所以離開了。”她悠悠説起當年事。
我打量她,穿鑲蕾絲的紫衫,碎鑽的鏈子纏在腕上,在燈下閃爍不寧。背後是紅的墻,白的百合。她言笑晏晏,不見歲月痕跡。
“怎麼走過來呢?像我新專輯裏的《缺口》一樣……時間吧。我也有爬不起來的那些時刻,但那些時刻,不必大聲呼痛,忍一忍吧。那個時候,音樂是非常好的朋友,它是那麼善解人意,你會直覺需要它,一旦它播放出來的時候……” 她深深吸一口氣,手勢莊嚴溫柔,“空氣裏都是了解。”
“很早就明白唱歌會是你一輩子的事情嗎?”
“絕對沒想到。我是一個沒有計劃也沒有太大智慧的人,從小我幻想當畫家,沒想到這支筆後來只是用來化粧,哈。當時是一個美工設計的學生,去參加一個歌唱比賽,也不是為了愛唱歌,只是那時台灣的學生人手一把吉他,於是我也去買,付錢之前看到海報,説是比賽前五名有吉他贈送,就去了,於是被唱片公司選中。”
那是1979年,她穿白衫黑裙,梳妹妹頭。
“那時你怎麼懂得《恰似你的溫柔》裏那種人生滋味?”我納罕。
她莞爾,“我的音色比較成熟,乍聽之下,好像很懂這首歌,那時還是一個大學生,怎麼會明白呢?但是我後來問梁弘志,你寫的時候你懂嗎?他説也只是當寫新詩來寫的。當然,這首歌唱唱唱,唱到現在,至少也有上萬次,因為歲月的成長,人總會在某個瞬間忽然明白什麼是‘破碎的臉’,什麼是‘浪花的手’ 。可是如果讓我在臺上穿不同的衣服,總是唱《恰似你的溫柔》、《不了情》,我不會滿足。從小看‘演唱’這兩個字,我就一直在想為什麼要加‘演’這個字?因為那是唱的極致。”
1998年她終於出演歌舞劇《天使不夜城》。那是當年她在主持《日正當中》的時候,説到電影與歌舞劇時,已埋下的願望。
“這一次,張力很大,起伏很強烈,還有那麼好聽的歌曲---還要跳mnbo。”她喜滋滋。
拉丁舞?
“要從頭學。第一個動作還勉強跟得上,到第八個,我已經從第一排到了教室的最角落,差點沒哭出來----天哪,難道我老了嗎?一看也沒有什麼好懷疑的,我是最老的一個。怎麼辦?這是我答應自己的事情。只有每天回去,自己用最笨的法子練,你看,這個。”
她給我演示“右臂右點腳踏跳”,我在心裏輕輕吹了一下口哨。
“每天睡覺前腳都要抽筋,根本沒有鬆懈的一刻,那半年,每天醒來時我都覺得自己根本沒有睡著,因為整個腦子都在唱那個歌舞劇的歌。”
“這是人生裏我會為自己鼓掌的一件事情,”她雙目閃亮。“演出那一夜,化了很濃的舞臺粧,戴上假發,穿上演出服和複雜的麥克風,我對著鏡子看著我自己,非常感動,對自己做一個加油的手勢。整個戲演完以後,謝幕的時候,全場起立,拍手,有人還掉了眼淚。我回到後臺,再看著鏡子裏面,眼淚汩汩地流下來。那種感覺真是……那一剎那我就完全了解什麼是自信。我覺得一個人要支持自己,去靠任何一個別人,都是很愚蠢的。”
我問她演什麼角色。
本世紀末“我演一個妓女,哈哈哈,而且是年華老去、生意不好的妓女,她在社會上是這麼卑微的一個人,卻一心一意想結婚。整場戲她出了很多笑話。到了最後還是悲劇的。男人怎麼會尊敬一個妓女呢?可是,她為什麼不能有夢想呢?”
一瞬間,我記起她唱“點亮霓虹燈,粉刷這黑夜不會那麼深,縱然心已冷也把愛當作真……”
“你也有過愛的挫折嗎?”我問。
“我就沒有我的角色這麼勇敢了,我只能承認我的失敗,但是我還不敢真正很有信心地迎接可能的成功,在愛情上。”她想了想自己的話,點點頭。空氣裏都是靜默和百合細若遊絲的清香。
我拿起桌上她那張叫《遇見》的新專輯,看看歌名,忍不住微笑。
她也笑:“是,這些歌都是80年代台灣很紅的歌,‘bala’歌,就是説爛得不能再爛了,但就像我不怕跟人家穿同一個款式的衣服,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什麼關係,又不是衣服穿我們,是我們穿衣服。從前當我聽到《張三的歌》、《驛動的心》時,我會想這些歌為什麼不是我唱的?這次,可以了。”
“有沒有更私人的理由?”
“嗯……這一首,”她指著《把悲傷留給自己》。“我父親去世的那天我才聽到這首歌。那時全家都很哀傷,我是長女,要處理很多事,一直忙忙忙,忙到下午五六點,我們要到山頂的佛寺去,弟弟問我吃飯了沒有,我才想起來,去了對面的商店,只是想買一瓶礦泉水和兩隻茶葉蛋。站在兩個貨架中間,忽然收音機裏就傳來陳升這首歌,我剛好聽到那兩句説‘我想是因為我不夠溫柔,不能分擔你的憂愁……’我站在那裏就哭起來了。因為我的爸爸一直把我當一個兒子在訓練,我知道他的遺憾是我不夠溫柔---可是……”
她的經紀人在旁邊指指手錶,她停下來看看我,笑吟吟。
最後我依記者俗例問她“最大的夢想”,以為會是在領終生成就獎時大家一起鼓掌下淚,享受殊榮。結果她説“到處去旅行”。
咦?她曾經説“家是我的堡壘”,一遍一遍。
“那時我在外面只想早早結束可以回家去,後來……大家都説你去過很多地方,真的嗎?我只記得後臺,還有飯店----天哪,連飯店我也記不清楚了,有一天,我真的試圖想回憶起芝加哥的飯店是什麼樣子,比利時的飯店是什麼樣子… …結果超過十五個以後,我完全混亂了。所以這個世界,我們好像到過了,因為有機票,還有行李上的很多標簽……但並不代表我們真的到過那個地方。以後我要真正去了解這個世界。
“至於家……對我們這些要到處走的人來講,只要按下手提音響上的play,你喜歡的音樂播送出來的時候,那個空間就是你的家。”
跟她握別。
回程車上,音響裏放《時間的河》,窗外燈火流麗之極,蔡琴的聲音醇厚純凈,“時間的河啊,慢慢地流……”,令人爛醉。那是1987年的歌了吧。
這麼多年了嗎?真不覺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