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返回首頁> | |||
 |
 1993年春節剛過,我在《中國廣播報》辦公室接到一個電話,是當時在電臺《午間半小時》工作的崔永元打來的,“小白,我的同學在電視臺要辦一個新的節目,挺缺人的,你過去幫幫忙怎麼樣?” 這不是一個什麼重大的抉擇,因此我一口答應下來。 在當時的北京新聞界,幹好本職工作之餘到別的媒體幫幫忙正開始成為時尚,再加上那時總感覺有多餘的精力可分配,嘗試點新東西總是好的。沒人會知道接了電話爽快的答應會讓我今後的生活發生大的變化,一個簡單的決定讓我走上一條與以前不太相同的路。 接下來和《東方之子》的製片人時間聯絡上了。當時的欄目還不叫《東方之子》,只知道是一個人物欄目,我的任務是去這個欄目當策劃,也就是幫助主持人設計一些問題,一起和其他工作人員進行人物分析。我不認為這很難,因為在幾年的報紙生涯中,我也採訪過好多人,再加上自己覺得這是一個副業,不可能把寶押在這個欄目上,因此心裏幾乎沒有什麼負擔。 時間很慎重,一個上午,他來找我,我給他拿了幾篇我過去採訪人物的文章,時間仔細看過之後,拍板,你來吧! 2月底,我去時間他們的大本營,當時他們一些人在北京亞運村的一座辦公樓裏租了一大套房子,為節目的開播作準備。大大的客廳被改造成演播室,兩張凳子固定了採訪人和被採訪人的位置,其他人住在另外屋裏,很有點小成本家庭作坊的意思。這就是《東方之子》剛剛成立時的情景。 剛一進屋,時間把我介紹給大家,我的年齡在那兒擺着,和“策劃”這個職稱似乎有點距離,我看得出屋內人士臉上那種不太信任的神情。正好我的一位大學同學在場,更是驚訝而直爽地喊道:轉了好幾圈,我以為找的是個老頭呢,原來把你找來了! 我並沒有感到尷尬,因為畢竟年輕還有些不知深淺,加上製片人時間和我談話的時候,淡化了我的工作職責,也沒有把太大的工作壓力給我。 工作就這樣開始了,當時的主持人都已到位,包括《工人日報》的胡健大姐、社科院的陸建華以及另外一位女學者,在他們的面前,我更是感覺到,我將把自己的服務工作幹好……就這樣我也慢慢地上了路,白天在報社正常工作,晚上和周末與未來的東方之子們打交道,日子倒也過得充實。 記不清是哪一天,時間找到我:“後天你出差去山東:採訪一個企業家,你做一下準備吧!” 我一時有點懵,什麼,我去採訪:沒有搞錯吧? 沒有,時間的態度很堅決,也沒有作什麼解釋就走了。聽了這個安排,當時組裏的攝像趙布虹倒是來了個預言:剛開始人們可能會不習慣你,不過你會慢熱的,能行! 我肯定不是千里馬,但就在這一位又一位伯樂的督促下,半推半就地上了電視路。 在去山東的火車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對自己來了個設計:我要做一個不穿西裝的採訪人,至少領帶是不能係的。但計劃沒有變化快,到達山東濟南,採訪開始前,時間看到我一身休閒裝束,便臨時給我借了一件西裝,領帶也打了上去,當時瘦骨嶙峋的我終於穿上一個寬大的西裝,晃晃蕩蕩地開始了我的第一次電視機採訪。想休閒一點的夢想沒有了一個好的開頭,以後幾番掙扎幾番被領導訓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步一步走上西裝革履之路,雖然彆扭,但一句“要對觀眾尊重”就慢慢打消了我的自由設想。 由於《東方時空》節目將在5月1日正式開播,因此我這次到山東採訪的對像是濟南鋼鐵廠的廠長馬俊才,一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最初和電視的磨合於我不是問題,既然不懂電視我也就沒了鏡頭感、攝像機在哪兒的顧慮,攝像師跟我説:“你只管像平時一樣採訪,別的事由我管。”就這樣,我的第一個電視採訪完成了。 在欄目開播前,要為自己的欄目設計一句廣告詞,當時沒有多少精雕細刻的時間,編導在機房外我在錄製間裏,現上轎現扎耳朵眼,第一句“濃縮人生精華”在我腦海中跳出的很快,大家也一致認可,而第二句就多少有些周折,一句一句地拋出一句一句地否決,直到“盡顯英雄本色”,大家才松了一口氣。於是從第一天節目播出起,“濃縮人生精華,盡顯英雄本色”這句《東方時空》欄目的第一個欄目廣告就開始每天和大家在早上見面。直到後來,隨着《東方時空》節目“平視”概念的增強,加上欄目廣告詞一句才最好,終於有一天,“盡顯英雄本色”這句話和觀眾告別,《東方之子》欄目和“濃縮人生精華”緊密為伴,這句話也成了欄目的一個標誌。 那時的我自然也沒有太長的設計。1993年5月底,我接到製片人時間的電話,問我想不想調進中央電視臺,我沒太考慮就拒絕了。“做電視”是副業這種概念在我當時的頭腦中還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當時在廣播報,我正籌辦着一張新報紙《流行音樂世界》,報社內部也把這件事當成了重點,甚至創刊號各個版的內容和樣式都設計出來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專門為此開了會,臺長也講了話表示支持,在會上“高舉起流行音樂這面大旗”很給人一種振奮。能把自己的愛好變成自己未來的工作,對我來説自然是件快樂的事,欣喜之中,覺得自己電視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沒底,於是就拒絕了時間的好意。 但走進電視看來還是我的宿命,過後沒多久,已經呼之欲出的《流行音樂世界》在當時一種對流行音樂依然不屑的氛圍中,被某位領導判了死刑。寄託了我的熱情和理想的夢碎了。我立即有了萬念俱灰的感覺,好吧,走。這個念頭一齣來,最後走進電視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問過我,假如那張報紙辦下來,你和電視説再見不會後悔吧?我想不會的,一來人生沒有假如,二來每條路都會有不同的風景。走上辦報之路自然會依照另一種規則欣賞着路邊的景致,也會有掙扎,也會有快樂,也許今天的自己會在那樣的一條路上尋找到另一種成就感。 可最終,我還是成了徹頭徹尾的電視人。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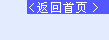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