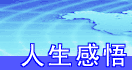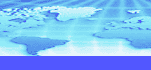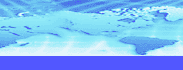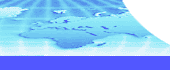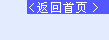|
人們習慣於把人生和音樂聯在一起,比如“歲月如歌”這四個字。
歲月如歌,生命的前進如同起伏的旋律,有激昂處的振奮,有低回時的消沉,但人生正是如歌般地從第一個音符開始便不間斷唱到尾聲,然後在歌聲散盡後,仍在世間留下一種對人生充滿些許浪漫的憂鬱,歌是美麗而短的,人生不也正是如此嗎?總是在不經意間一切都已流逝過去,最美的東西往往不可救藥地留在記憶裏。
好在音樂能幫我們回憶。
歲月如歌對我來説絕不僅僅只是一種比喻,它有著更真切的含義。
回憶中的生命之路,總是要有很多路標,提醒你:在那一個路段上曾經發生過怎樣的故事和曾經擁有怎樣的心情。音樂就是這樣的路標。
一段熟悉的旋律或是一首好久不唱的歌,一旦不經意地在身邊的哪個角落響起,我腦海中便很快浮現出與這段旋律相對應的歲月和心情,然後沉醉一會兒,晃晃腦袋從記憶中退出,再慢慢地上路。在這個時候,音樂於我,是生命回放的遙控器,而且屢試不爽。在音樂這種路標的提示下,回憶很少出錯,幾乎可以密不透風地把我這20多年的人生經歷很快串聯起來,然後讓我也能擁有歲月如歌的感慨。
每當《祝酒歌》、《邊疆的泉水清又純》、《潔白的羽毛寄深情》這些歌曲的旋律飄來,我馬上就會讓思緒飛到70年代未、80年代初,當時哥哥去北京上大學,家裏就我和母親相依為命,媽媽下班的時間總要比我放學晚一些,於是在東北嚴寒的冬夜,由於我不會生火,家中自然很冷,我縮在收音機旁邊聽著這些歌曲等母親回來。在那樣的冬夜裏面,這些歌曲天天溫曖著我,成了呼吸都會産生哈氣的屋旦,讓我不再孤獨的朋友,而當時,我不過是十多歲的一個少年。
鄧麗君在泰國離世,好多中國人會心頭一緊,因為她的歌聲陪著我們從精神的荒蕪中慢慢走出。我也一樣,鄧麗君的歌聲一響起,我就能記起舊的大墻剛剛倒下的歲月裏,偷聽鄧麗君的有趣故事。在那時,不知翻錄過多少遍的磁帶,由於上面錄的是鄧麗君的歌,因此依然被當作寶貝。和同學互相交流收聽“澳洲廣播電臺”中文節目的感受,因為在那裏每天都可以聽到鄧麗君、劉文正的歌。當然鄧麗君的歌聲響起,也馬上能想起身邊手提錄音機,穿喇叭褲、戴麥克鏡的年輕人。在當時,我猜想,自己心裏是羨慕他們的。可能正是這樣的相依為伴,鄧麗君的唱片成了中國市場上的長銷貨,她身邊的歌手不停地變換,而她依然跨越歲月在那裏憂鬱地微笑。似乎每天都會有男男女女將她的歌聲再度領回家中,去重溫多年前的一段旋律,重溫自己成長中的一段記憶。我也是如此,在告別鄧麗君十幾年之後,又買了一套她的全集,偶爾聽聽,回憶的底片便會泛黃。
而一唱《我的中國心》,我就馬上想起1984年那一個除夕,吃完年夜飯,我急匆匆地到鄰居家裏在那個不大的黑白電視機前過了第一次沒放鞭炮沒在雪地裏瘋玩的除夕。也就在那一天,認識了張明敏,熟悉了《我的中國心》,然後在之後很長的時間裏,嘴裏哼的都是這首歌。
到85年上大學後,同學之間傳唱的是周峰的《夜色闌珊》和蘇芮的《是否》、《一樣的月光》、《酒幹倘賣無》。上了大學要顯得比中學時成熟得多,蘇芮的一身黑色行頭和與眾不同的聲音很符合我們的口味,更何況“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這樣的唱詞,讓我們意識到生命已經進入到思考的季節。
4年後,當然是在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齊秦的《大約在冬季》中從校園中出走。我奇怪的是這兩首一動一靜一個憤怒一個感傷的歌,為什麼能如此協調地在那個夏季為我們送行。我猜想這兩首歌和那段歲月的聯絡,在我同齡人的記憶中都相似的。
當童安格《讓生命去等候》隨風飄來的時候,我正在北京的週口店鄉鍛鍊,當時的狀態何嘗不是讓生命去等候!與此同時,王傑《一場遊戲一場夢》也開始讓我們反思走過的一些道路:莫非付出了激情的一些舉動都是夢一場,莫非我們正值青春便遊戲人生?
然後是黑豹、唐朝,那重重的敲打和高亢的呼號竟成了我去電視臺之前那一段日子的背景音樂。迷茫,希望看到更好的未來,週遭沉寂的世界開始慢慢甦醒,人們心中開始有話要説,唐朝與黑豹的聲音成了表達我心情的最好替代品。
再然後,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悲愴)交響曲》的第一樂章。那是1994年冬天,我正在採訪12位中國知名的老學者。天天準備到夜裏一兩點,眼前的故事都是些歷史片斷,12位老學者,12座人格的碑。那段準備採訪的日子竟怎麼也不能和老柴的《第六交響曲》分割開來。看到老學者的名字就想起老柴,聽到老柴的曲子就想起採訪老學者的那段日子,回憶和音樂就是如此奇妙地交織著。
人過30之後,是巴赫的《平均律》,是舒伯特的鋼琴曲……我將用更長的歲月去填上這省略號代表的部分。
而以上這些只是回憶中的幾個片斷,動用的路標還很少,沒有提起的旋律和歲月太多了。我相信每一個心靈中,如此的旋律性路標都有很多。比如我發現,當蘇聯的一些老歌旋律唱響的時候,母親的神情就會與往日不同,該是在熟悉的旋律中,母親又回到50年代的大學生活了吧?而當妻子聽到鄭智化的歌時,她的話就比平時多一引,因為在她畢業時,校園裏的流行旋律就是鄭智化唱出的。
誰的歲月中都有歌,不管你是喜歡音樂還是不喜歡。當然喜歡音樂的人回頭時,旋律會更豐富一些。想一想也算幸福:一路艱難的奔波,在回憶時總有一些優美的旋律陪伴著,行走的也就不算孤獨。音樂就是這樣一位不動聲色的朋友,不打擾你卻暗暗地撫慰你,怕你忘掉什麼因而時常用自己的旋律提醒你,一路行走,歲月中有歌,路,艱難些,也還算好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