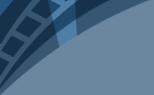|
“人總是在改變,而鳥兒卻從來都不改變。”2004年1月9日,雅克�貝漢輕鬆地坐在北京國際飯店的會客廳裏,銀發飄逸,仿佛是一位剛剛收攏了翅膀的天使。“它們對於飛翔是如此的執著,對於自由是如此的渴望,它們從來也不停止振翅的飛翔。”雅克陶醉地鼓動著雙臂,仿佛重又回到了五千米的高空之上,“飛過高山,飛過大海,它們奮勇地飛著。讓它們停止飛翔可真難!因為它們沒有時間停歇--它們總是在飛翔的奮爭之中。”
作為震撼了全世界電影觀眾的紀錄片《遷徙的鳥》的導演,這位60歲才贏得“法國新銳導演愷撒獎”的老人如一位溝通人間與鳥界的通靈薩滿,以他光影的詩篇為我們洞開心扉:“在人類的夢想裏,總有一個自由的夢想--像鳥兒一樣自由飛翔的夢想。”而我們這些早已在靈魂上折斷了雙翼的鳥兒,在某一個清晨或午夜,在登上飛機或走出地鐵站的一瞬間,又或者,在雅克�貝漢精心營造的翩然夢境裏,是否也會感覺到一種久違的衝動呢?想飛!
想飛。1997年某一個秋日的黃昏,當了近40年電影演員與製片人的法國人雅克�貝漢,注視著一群叫不出名字的季候鳥嘎然劃過巴黎的上空,忽然想飛。他知道這思想無比美好,而美好的東西卻往往轉瞬即逝--這位曾經在《天堂電影院》裏扮演過成年以後的“托托”、曾經為那些落英繽紛的親吻鏡頭淚流滿面的老演員決定馬上付諸行動。他起飛了,而這一飛就是整整四年。和遷徙的鳥兒們一起,雅克飛越廣袤的非洲與美洲大地,橫穿浩瀚的太平洋與大西洋,他偶爾停落在冰雪崢嶸的喜馬拉雅山,有時也歇腳于撒哈拉沙漠弧線完美的沙丘之上,或許又曾在某個暴風雨的前夜,讓一隻名叫喬納森的年輕海鷗感到深深的震驚。
“如果你是鳥兒的話,當你飛累的時候可以隨時找個地方歇歇腳,但如果你在一個機械裏,而它又情況不佳,你就哪兒也去不了。”雅克�貝漢微笑地談論起他唯一的飛行缺憾--人類難得有對其他生物自愧不如的時候,飛鳥的翅膀卻恰恰正在此列,“我們曾有過七次墜機的事故,大都是有驚無險,但當你在幾千米的高空和鳥兒一起飛翔的時候,你只會感覺到無比愉悅,而那時載著我們的機器會怎樣?隨它去吧!”
“鳥兒從來不説什麼,它們只是堅持去飛。”雅克�貝漢用他四年的堅持留給統計家們一長串耐人尋味的數字:400多人的拍攝隊伍,4000多萬美元的製作成本,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往來奔波以及460多公里的膠片長度。在《遷徙的鳥》這部作品當中,雅克也遵循了鳥兒寡言而絢爛的“鳥文主義”傳統:所有的旁白加在一起,也沒有超過40句。
這是一部“視覺係”的電影,一部“印象派”的電影,或者説,它帶給人們的是一場宛如夢境的親身經歷--而按照詩人們的説法,“夢是可以不押韻的”。至少在銀幕上,我們還從未如此安詳地與鳥兒們親密接觸,和它們一起並肩飛翔在湛藍的天宇,不是作為一粒子彈,不是這些美麗精靈噩夢中的加害者,而是它們當中的一員--另一隻明月入懷、無心可猜的季候鳥。這是一個“莊周夢蝶”般的法國之夢,或許真有過那麼一個瞬間,飛行在雲端的雅克�貝漢也曾如那位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哲人一樣,弄不清究竟是自己化作了飛鳥,還是一隻在遷徙途中打盹的鳥兒,夢見它變成了一位滿頭銀發的法國人:雅克�貝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