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6年02月20日 15:07 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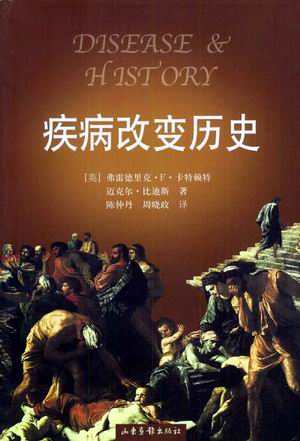
| |
1998年7月17日,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的遺骸(除皇太子阿歷克謝和第三個女兒瑪莉婭之外)在他們被殺八十年之後的同一天安葬于彼得堡的聖彼得-保羅大教堂。簽署這項安葬命令的葉利欽也參加了這件“極富戲劇色彩、也相當令人傷感”的葬禮。事後,他本人在日記中沒頭沒腦地這樣寫道:“我們實際上喪失了體驗歷史的完整性和連續性的可能。我多麼希望在不遠的將來這一切都能夠得到恢復。”(《午夜日記》第十章)這裡我的理解是,葉利欽既是在感嘆命運無常,似乎也是希望俄羅斯能夠重新回到羅曼諾夫王朝的輝煌時代。
1917年,羅曼諾夫王朝的垮臺是世界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西方學者和蘇聯學者對它垮臺原因都有過大量的分析,卻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歷史規律”之外的偶然性。人們非常熟悉的一種觀點就是列寧在《遠方來信》所講的,維持了許多世紀的沙皇君主制度在八天之內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是階級鬥爭和帝國主義戰爭。(《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頁)如果有人説,導致羅曼諾夫王朝最後垮臺的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也不是階級鬥爭,而是非常偶然的血友病,我們恐怕就會感到驚奇,這個聽起來有點天方夜譚式的結論是醫學史家弗裏德里克�F�卡特賴特(F.Cartwright)和歷史學家比迪斯(M.Biddies)在所著的《疾病改變歷史》(Disease & History)一書中對這場震撼世界歷史事件的看法,而且這還僅僅只是疾病改變歷史一系列事件中的一個。該書1972年由紐約的Thomas Y.Crowell 公司出版,2000年修訂後又由英國出版歷史著作的薩頓出版社(Sutton Publishing)出版,最近它又被譯成中文,成為山東畫報出版社“醫學與文化”叢書當中的一種。表面上看,這類從醫學史家的角度觀察人類社會發展的另類歷史書籍如今走紅,受到了近年SARS、禽流感等傳染病影響。其實,醫生和歷史學家的有很深的淵源關係,至少我國先秦時期掌管歷史的巫和醫生是不加區分的,所謂“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論語�子路》)“醫”的繁體字就寫作“醫”和“毉”,《廣雅�釋詁》雲:“醫、覡,巫也。”更重要的是他們都以人為研究對象,都要面對疾病對歷史所産生的影響,所以在西方史學界醫學史始終佔有一席之地。
疾病會影響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在國內讀者當中也不是一個新話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新華出版社曾出版過一本由法國學者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學者皮埃爾�朗契尼克寫的《病夫治國》,專講老人政治的弊端。作者認為,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專制社會,只要存在魅力型的領袖,其精神和肉體的健康足以影響歷史進程。書中舉了列寧、丘吉爾、戴高樂、羅斯福、肯尼迪、約翰遜、艾森豪威爾、赫魯曉夫、毛澤東、納塞爾等二十多位領導人身體不健康的例子來説明領袖身體或者精神上的麻煩能夠改變國家的命運,而由此造成的後果,總是要由無辜的民眾來承擔。當時我國正在醞釀廢除領導人的終身制,這本內部出版物契合了這一時機影響不小。但是該書的價值取向是英雄史觀,著眼處是個人對歷史的影響,疾病只是作為一個偶然因素來證明英雄作用於歷史。
在《疾病改變歷史》這本書中,卡特賴特和比迪斯就與前者不大一樣,他們指出:“疾病不僅對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響,也對普通大眾産生影響”,“認為疾病是引起某種歷史巨變的主要原因這種説法是荒謬可笑的。”(《導論》)所以他們主要關注的是那些影響人類種族命運的疾病造成的影響以及用這些疾病的傳播來説明時代特點。在醫學史家和人類學家的眼中,疾病是人類文明發展過快的衍生物,它和戰爭、饑餓交織在一起改變歷史的軌跡。如黑死病、雅司病(yaws,是一種形態似梅毒螺旋體的雅司螺旋體〔Treponema pertenue〕引起的慢性接觸性傳染病,主要在中非、南美、東南亞一些熱帶地區流行,也偶見於溫帶)、梅毒、霍亂、傷寒、天花、艾滋病等惡性傳染病都是對普通大眾發生影響的疾病,它們不斷調整和改變人類的行為方式。在人類的早期社會,疾病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長的作用。一般來講,只要文明中心區的人口向邊緣擴展時,就會有傳染性疾病在沒有抵抗力的居民中間傳播,這就如同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的生物入侵一樣。研究還發現,非工業社會流行性疾病有季節性,使人口死亡率在適中和較高之間波動,使人口增長維持“繁榮-蕭條”的平衡。(唐納德�L�哈迪斯蒂:《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頁)在近代工業文明和今天全球化的時代,疾病的傳播已不按照季節、地域、國家和種族來劃分,它是跳躍式傳播。像埃博拉病、軍團病(Legionnaire’s Disease)、艾滋病、禽流感和SARS都可以利用現代交通工具瞬間傳播到他地,其影響也不限于某一部落和某一地區,生態、環境、政治、經濟均受到波及。作者認為,“艾滋病最終爆發的性質和速度顯示,人們的流動性增強以及其他行為上的改變(包括性行為更加‘放縱’),這有助於説明我們所處的‘全球化’時代的特點。”(第237頁)這個特點就是傳染性疾病增加了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潛在危險。2003年,SARS突然爆發,在中國和世界都産生了社會的恐慌就很能説明問題。
大規模的傳染病是人類文明的伴隨物,因此不是天災而是人禍。農業文明的集體生活方式和發達的飼養業就是造成物種之間病毒交叉傳染的原因,只是農業社會的人口流動有限,疾病一般都是區域性的,在內陸地區所能造成影響也有限。如中國文獻最早記載的時疫發生在公元前674年,是齊國傳到魯國的近鄰傳播,其他國家似乎沒有受到影響(“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癘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公羊傳�莊公二十年》)。但是在交通發達的沿海區域和戰爭時期,一個地方性的疾病説不定就能引起了歷史的變化,作者舉了雅典和羅馬的例子。
雅典在公元前431年爆發了使希臘文明衰落的伯羅奔尼撒戰爭(431~404 BC),不料第二年就發生瘟疫。據修昔底德説,瘟疫是起源於上埃及(埃塞俄比亞),再傳到埃及和雅典。“人像羊群一樣地死亡”,“由於瘟疫的緣故,雅典開始有了空前的違法亂紀的情況。”(《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141~42頁)這場突如其來的瘟疫一下子就把雅典的開明政治破壞了,不僅政治家伯裏克利因此死去,雅典海軍死亡四分之一,大喪元氣。卡特賴特認為這場瘟疫最終使雅典敗于斯巴達(第8頁)。羅馬遭受傳染病的打擊更為慘重,在馬可�奧略留皇帝(Marcus Aurelius161~180)任內爆發的著名的“安東尼瘟疫”(又稱蓋倫醫生病),它是羅馬軍隊鎮壓敘利亞後帶回來的疾病,軍隊在這場瘟災中損失了十分之一,而十五年之內它導致了羅馬帝國本土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皇帝本人也在瘟疫中死去。蓋倫(Galen 129~216)所描述的病症是高燒、咽炎、腹瀉並且皮膚化膿。有學者據此認為這是天花最早流行的記錄,病源是來自蒙古,這也是迫使匈奴人西遷的原因。但作者認為它不是天花。在公元250年,羅馬又爆發了另一場傳染病——西普裏安大瘟疫(the Plague of Cyprian),它因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裏安(Cyprian 200~258)的記載而得名。它的症狀是腹瀉、嘔吐、潰爛、高燒,卡特賴特認為它是斑疹傷寒,是從埃塞俄比亞、埃及和羅馬在北非的海外殖民地傳播而來。它持續時間有十六年,高峰期羅馬城每天死亡的人數達到五千。據作者講,羅馬的這兩場瘟疫産生了一個改變歷史的深遠後果,這就是基督教因此成為了世界性的力量(第17頁)。
從歷史上看,全球化的起點應該始於開闢去美洲的新航路,它的副産品就是把舊大陸的傳染病天花、麻疹傳到美洲,同時也把美洲的梅毒一類疾病傳到其他地方。在科爾特斯(Hernando Cort岢s 1485~1547)征服墨西哥和皮薩羅 Francisco Pizarro 1471~1541征服秘魯時,他們所帶來的傳染性天花等病毒都成為印第安人致命殺手。當時參與攻克墨西哥的貝爾納爾�迪亞斯曾寫到,他們進城後,大街小巷儘是死人,“我們只能在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屍體與頭顱之間行走,……墨西哥城死去的人實在太多,……散發的惡臭令人無法忍受。”(《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下)》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17頁)其實,當時科爾特斯的兵力遠遜於守方,卡特賴特和比迪斯認為美洲居民缺乏對付舊大陸疾病的抗體,殖民者的勝利是因為大多數印第安人死於疾病。這樣大規模的死亡慘劇造成了印第安人的恐慌,他們以為是天神的復仇而喪失了對殖民者的抵抗意志,使之入無人之境(第76~79頁)。從史料記載來看,墨西哥的人口從征服前的2000萬左右到十七世紀不到200萬;秘魯則從700萬減至50萬,整個新大陸的人口下降到只有原來的10%,多數是因為無法抵抗傳染病而死。它産生的一個間接後果就是造成美洲勞動力的緊缺,並引發了帝國主義歷史上最骯髒的黑奴貿易。順便説一下,戰爭引起的傳染病爆發的類似恐慌在我國也發生過。金開興元年(1232年)元兵攻打開封,封城之後,百姓無法出城造成大疫,“諸門出死者九十余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金史�哀宗紀》卷17)我們知道,北宋開封最繁盛時,人口也不過150萬,這場瘟疫至少死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二。同年12月,金人只好放棄開封遷蔡(今河南蔡縣),一年後,蔡就被蒙元拿下,金亡。史書沒有講金人滅亡之前流行的瘟疫是什麼,從疾病迅速爆發和死亡的慘烈來看,這應該是戰爭造成的人口在短期內大量集中,衛生惡化引起了鼠疫一類的疾病。沒有它的流行,宋、金、元的歷史恐怕又不一樣了。
在討論疾病對大眾的影響及與歷史之關係,作者寫了很有意思的一章,即“暴民癔症和大眾暗示”。一般來講,鼠疫、天花一類影響肉體的傳染病很容易被學者注意,大眾精神性的疾病就不那麼容易被發現。作者講的大眾精神性的疾病就是所謂的“暴民癔症”,這是一種集體性的歇斯底裏現象,在群體內他們互相模倣,害怕被看成另類;群體以外則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個人發生症狀,會連鎖性的傳染給別人。法國的聖女貞德(Joan of Arc 1412~1431)和希特勒在作者眼中都被認為是有癔症的人,他們在特定的場合能夠感染許多人。貞德年幼時有幻聽、幻視的症狀,即現在所稱的“美尼爾氏綜合症”(第216頁)。作者是英國人,他們對貞德的看法,法國人肯定不高興。但是有一點他們是對的,這就是在英法百年戰爭中,法國人在七十多年的反抗不成功之後,具有通靈能力的貞德自然很容易成為民族復興的希望。我想,當時即使沒有神靈也應該創造一個出來,貞德不過適逢其會。從宗教現象學和人類學的研究來看,我認為貞德所造成的集體性的癔症是所有的社會之常態。書中也舉了中世紀德國的“舞蹈病”和低地國家舞蹈狂熱,它們的表現形態與十九世紀下半葉北美流行的印第安人反抗殖民、恢復土地的“鬼舞教(Ghost Dance)”基本是一類事,都是相信可以獲得超人力量的幫助。我們知道,人類對未來和未知的恐懼需要利用超人力量以預防和應付社會危機,只有盡可能的接近“神聖”才可以避免危機。歷史上所見的各種神啟、理想主義和烏托邦都具有“神聖”、“絕對正確”的共性,這既是人類對恐懼的本能反應和“恐懼”之冠冕堂皇的遮羞物,也是暴民癔病的心理基礎,所以任何社會都無法排除集體癔病。貞德以“神聖”名義倡導的抵抗在世界歷史上的各個時期都以宗教運動的形式上演過,像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義和團、紅衛兵運動都是如此。作者把它劃入疾病一類,與其説是這類大眾性疾病改變歷史,還不如説它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希特勒的情況與貞德有一點區別。作者説他年輕時有妄想症,我想這種“妄想”恐怕不能説是精神性疾病,較為中性的説法應該是“幻想”。它是人人都有的,問題是出在整個德國在一戰之後都存在希望國家儘快擺脫戰敗恥辱的“暴民癔症”狀態,大眾就很容易被希特勒的宣傳機器所引導,這裡面起主要作用的是納粹的宣傳機器而不是希特勒的個人魅力。希特勒純潔雅利安人的想法和使納粹黨成為德國唯一合法政黨 、“以消滅一切與其團夥類型不一致的每個人”的運動,經過納粹宣傳機器的放大,就激發了人類恐懼被視為另類的心理,造成了集體恐懼的效果(第229頁)。在宣傳機器密集的“暗示”下,“愛國主義”、“反猶主義”成為納粹意識形態擴張的最好掩飾,而能夠保持理性的人往往會被當成另類,他們在暴民癔症的威脅下,最好的辦法就是遠走他鄉。
另外,我們知道當時德國支持納粹上臺的是多數人,大量的知識分子也參與其中,如卡拉揚、海德格爾等人。作者卻沒有講為什麼號稱社會良心的德國知識分子整體也喪失了理性,默許了納粹政權?僅用希特勒個人的精神妄想和“大眾暗示”是不能完全解釋的。儘管事實上大眾心理從來都受到權勢話語的誘導和指引,理性本身也由控制話語權的集團來規定,但是知識分子的意義本身就在於從體制內部質疑社會習以為常的真理。如果説普通人容易受到“大眾暗示”影響的話,那麼德國的知識分子對“大眾暗示”應該是最具免疫力的群體。我認為這是納粹壟斷輿論之後,“大眾暗示”實際上變成了“大眾威脅”。在納粹宣傳機器面前,知識分子要麼被消滅,要麼在宣傳的暗示下相信納粹的“愛國主義”、“反猶主義”就是理性的行為。在絕對的輿論控制下面,德國知識分子的每個個體在他專業之外仍然等同於一無所知的“暴民”。一般來講,只要普通人相信權威,這就會引起暴民癔症,這與權威本人有沒有精神性疾病關係不大。這裡可以舉一個美國的例子。1938年10月25日晚上8點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聽眾在廣播裏聽到了以新聞方式播出的火星人登陸地球的消息,儘管當時美國還有多家新聞社説那是個玩笑,但整個美國東到緬因州,西到加州都有人認為世界的末日到了。事後,普林斯頓大學的調查表明,有170萬人認為這是新聞。如果認為只有教育程度低的人被騙那就錯了,收聽的大學生有28%,高薪階層有35%都信以為真(威廉�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274~78頁)。這個例子可以説明人類相信權威的天性是集體非理性(暴民癔症)的原因。在專制極權社會,權威的誘導就更加容易引起社會性的瘋狂。
近代以來,文明快速增長,人口流動和戰爭規模都是空前,疾病對歷史進程的干預無處不在,而影響往往出人意料。作者講了許多故事,我感興趣的二個都與俄國有關。1812年,拿破侖為了建立統一的歐洲率領60萬大軍進攻俄國,結果法軍失敗,回國的不到4千,這不僅終結了拿破侖統一歐洲的帝國夢,三年以後皇帝本人也被送到了聖赫勒拿島監禁。歷史學家對這這個結局有多種分析,卡特賴特和比迪斯給出的結論是法軍敗于斑疹傷寒。法軍雖然有良好的醫療系統,這種只流行于俄國和波蘭的疾病卻造成了拿破侖軍隊的大量減員,法軍當年6月進兵,7月因病死亡和喪失作戰能力的就有8萬。在進入莫斯科的一星期當中死於傷寒的有1萬多人,十分之七的部隊倒在了路上(第106頁)。拿破侖東征俄國的失敗使原有的帝國也隨之而分崩離析,但是歐洲人統一的夢想並沒有完結。歷史過了近200年,西歐的勢力再次來到俄國的門口。2004年5月1日,塞浦路斯、波蘭、匈牙利、捷克、立陶宛等10國加入歐盟,歐盟東擴的第五階段完成,與俄國形成對峙局面。西方這次用的是經濟武器,而在現代醫療系統面前斑疹傷寒已不是問題。今後東、西歐如何互動,應該是一段充滿戲劇色彩的歷史,令人關注。那麼俄國該如何應對呢?我們在前面提到過葉利欽在末代沙皇葬禮上的嘆息,這應該反映了一般俄羅斯人的想法,他們現在所希望的大概就是能在普京的領導下儘快重振羅曼諾夫王朝的雄風。
在卡特賴特和比迪斯眼裏,羅曼諾夫王朝不是亡于帝國主義戰爭和政治腐敗,而是亡于血友病。從疾病對歷史的影響來講,這種看法不能説沒有依據。我們知道西方的君主制度有一個為了保持血統的高貴,王族之間互相通婚的重要傳統。在現代遺傳學看來,這種通婚如果一方有基因性疾病,就會遺傳給其他王室後代。在西方史學家眼中,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1837~1901)是最不可能把布爾什維克送上權力寶座的人,但是恰恰因為維多利亞本人患有血友病,並通過外孫女艾莉克斯與沙皇尼古拉的聯姻,將血友病傳給了他們的兒子阿列克賽。從他們結婚的這一天起,羅曼諾夫王朝的厄運似乎就被維多利亞的血友病決定了。
血友病是一種血液中缺少凝血因子的疾病,以致患者受傷後,因凝血機能差容易因失血過多而死亡,並多見於男性,女性只是把它遺傳給後代。維多利亞女王患的是“甲型血友病”(先天性凝血因子VII缺乏),她的一個兒子死於該病,二個女兒把病傳給了兒子和孫子。小女兒生的二個兒子都死於血友病。大女兒生了五個女兒,最小的一個就是嫁給沙皇的艾莉克斯。作者在介紹維多利亞的譜係時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家族遺傳性疾病,由於維多利亞以前的祖輩沒有此病,她的身份一直受到懷疑(第194頁)。2002年9月,英國傳記作家A�N�威爾遜(A.N. Wilson)根據王室病歷檔案在新書《維多利亞女王》(The Victorians Hutchinson 2002.)中指出此病來源於維多利亞母親的情人,這個質疑英國王室合法性的結論,曾被國外媒體炒作一時。而在當時,沙皇尼古拉與艾莉克斯是一見鍾情,他父親亞歷山大雖然想讓他娶一個東正教的公主,但是愛情的力量和老沙皇因病快死,使這對戀人終成眷屬。可是羅曼諾夫王朝的麻煩也就接踵而至,他們的唯一兒子阿列克賽生下來就患有血友病。
普通人得了血友病,影響限于家族。皇儲阿列克賽患有血友病,這就使母親艾莉克斯,即俄國的皇后亞歷山德拉陷入焦慮和惶恐之中。在挽救阿列克賽方面,皇后只相信一個人,這就是來自西伯利亞的巫師拉斯普廷(G.Rasputin,1871~1916)。在羅曼諾夫王朝的宮廷史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個性格懦弱、熱愛家庭的人,這就註定使他成為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對妻子的寵愛和對兒子的關心使這位末代沙皇逃避宮廷生活隱于聖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亞歷山德拉皇后又是一個喜歡權力的女人,兒子患有血友病,使她對兒子健康的擔心變成一種信念,兒子必須成為像彼得大帝那樣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1905年俄國發生資産階級革命後召開了國家杜馬(議會),這是通過立憲來取消沙皇專制,使俄國走向議會民主道路的第一步。當時俄國的國家杜馬並沒有西方議會那樣的權力,但它還是讓沙皇一家不愉快。最討厭國家杜馬的就是皇后亞歷山德拉,原因之一是杜馬要調查拉斯普廷的醜聞,之二就是杜馬對皇權的限制妨礙了兒子阿列克賽成為一個強大的君主。1915年,皇后正式插手政府事務,結果全國都把仇恨的情緒集中在沙皇、皇后和干預朝政的拉斯普廷的身上。1916年年底,宮廷貴族以為除掉了拉斯普廷,沙皇夫婦就會回到理性的狀態,他們派人暗殺了拉斯普廷。結果卻恰恰相反,沙皇本人因此身體垮掉,失去了對軍隊的有效控制,他所有的顧問和親信都被皇后免職。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成為孤家寡人的沙皇退位,全家被囚禁在皇村。俄國走英國君主立憲道路的機會就此徹底破滅。十月革命之後,沙皇全家被押往烏拉爾東的葉卡婕琳娜堡,1918年7月17日淩晨沙皇一家七口,還包括醫生鮑特金、廚師哈裏托諾夫、僕人特魯普和傑米多娃一共11人被當地烏拉爾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令處決。
如果沒有血友病,俄國的道路會不會一樣?作者顯然是認為是的。他們認為,歷史在經過八十年之後重新安葬沙皇就標誌著政治和解,而這一切又使人回想起革命和內戰的痛苦和隨後的古拉格的恐怖體系。“人們不禁會産生疑惑,從一個無能的沙皇獨裁製度轉變為一個更具壓制性的共産主義政權,對整個世界尤其是對俄國是否有益。”歷史無法假設,但是從今天俄國的目標來看,它確實繞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羅曼諾夫王朝的起點,就像作者所説,血友病使俄國錯過了一個大好的時機。俄國在歷史上走的彎路對西方其他國家來説或許是有益的,這正好為它們騰出了發展的空間。他們因此感慨到:“這或許是維多利亞血友病基因留下的真正遺産。”(第212頁)在我看來,這裡面總有一點幸災樂禍的色彩。從俄國後來的混亂和專制悲劇來看,它是制度性的缺陷造成的,把羅曼諾夫王朝的崩潰説成是血友病造成的,恐怕誇大了疾病對歷史的影響,是一種變相的英雄史觀。羅曼諾夫王朝雖然無法躲過血友病,這可以説是不可抗拒的天災。但是沙皇專制制度卻是可以人為改變的,俄國在1905年沒有能夠進行民主制度的建設,沒有實現君主立憲的制度轉變,是專制政權不會主動放棄權力的本能所致,這應該是人禍而不是疾病改變歷史的問題。
醫生和歷史學家都有一個以人類為研究對象的共同點。傳統的史學家注重的是歷史的宏大敘事,很少關注疾病、環境、生態等社會學方面的問題,而醫學史也往往多是醫療技術的發展史。《疾病改變歷史》把眼光放在了疾病對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上面,這與二十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歷史著作的敘述中心由王朝政治轉向社會生活是一致的。它的最大的優點就是結合了醫學和歷史的長處,從醫學的視角來看待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問題。作者認為,伴隨人類文明的瘟疫、饑荒和戰爭這三個問題分別是人體失調、環境失調和大眾精神失調所致。儘管這種結論還可以討論,但該書的著眼點是現代化或者全球化背景下的疾病傳播問題,破除所謂現代科學可以戰勝任何疾病的盲目樂觀精神,是非常正確的,值得我們警惕。作者一個主要觀點我很贊成,從疾病對歷史的影響上看,多數疾病的大規模流行,並不是天災,而是人類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本身存在問題。像癌症、艾滋病等的迅速蔓延都與工業化和全球化有密切關係,人類以為自豪的醫學技術也並不能幫助人類免除疾病的打擊,抗生素濫用的副作用反映出“醫學取得的成功,最終證明其本身也成為問題的根源。”人類對物質的貪婪,對現代技術的追求,使人類自己跑到了文明狀態的前面。我們不受限制的繁殖、弄臟自己的環境、耗盡有限的資源,我們就只有接受饑荒、戰爭和瘟疫的懲罰(第242頁)。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疾病是人禍,也是天譴。
(《疾病改變歷史》,〔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賴特、邁克爾�比迪斯著,陳仲丹、周曉敏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2月版,20.00元) (來源:光明網)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