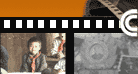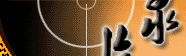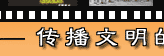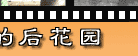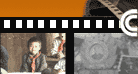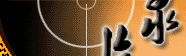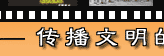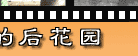像一尾隨波逐流的魚捲入了漩渦,我遇到了紀錄片的誘惑。
兩年以前,我還在學校裏,有一次聽了一場報告,是一位紀錄片人主講的,他講了一位攝影師在航拍不慎墜地時還忠實地用攝像機記錄下墜落的過程,我被感動得一塌糊塗,對這份如此迷人的職業心生嚮往。
不料那時種下的種子真的得到了發芽的一天。現在,我真走進了紀錄片部,好似誤入藕花深處。這裡如同一條夏天的鄉間小路,綠草叢生,風景悠長。
我最先見到的是穿著一件亮藍與亮黃顏色相間的外衣的陳曉卿(紀錄片欄目製片人),他的髮型酷似潘長江,頭髮短短的,額前部分尖尖的。起初我誤以為他是個小青年,後來才知道他比那位看來相當成熟的肖同慶(欄目主編)還大一歲呢。因此,看到高峰(CCTV社教中心主任)的書説,你看著最不像導演的那個人,就是紀錄片的導演,我立即心領神會。陳先生説話有時候並不流暢,可是年輕的時候還為自己的片子配過音;他的鋒芒在於,博聞強記,腦子好極了。
肖先生嚴肅的時候很儒雅,笑起來卻很頑皮,他是研究魯迅的博士,筆鋒也有點魯迅的味道,平時總能夠用驚人的語句表達幽默。但是筆調一冷,面相似乎難免會相對"成熟"一點。他最敏感的話題是他的身材,説,見到女人不要問年齡,見到我,不要問體重,也不要説增肥的方子。
接著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留著不太氣勢的絡腮鬍子的人,頭髮濃密,看起來有點像蒙古族人(後來我知道,他雖長在內蒙,可卻是漢族人),他的眼神有著十分柔和的仁慈, 讓人産生悲天憫人的聯想;語調溫和,批評人也是和顏悅色的派頭。當我看了《最後的山神》時,對於那個令人尊敬導演曾發生很多想象,所以,當我得知這個溫和的稱我為"丫頭"的人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導演孫增田,激動得趕緊上前去套瓷:我非常、非常喜歡你做的片子。他微微地看著我,連一星點笑意都被真誠的眼神給蓋住了,然後,滿足了我想看看他其他的片子的請求。
孫先生不抽煙,他的辦公室也相當於無煙室,當我在煙霧繚繞的957室感到呼吸困難,就跑到他的辦公室953去溜達。在那個辦公室裏,我看到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叫做《江湖飄》,圖文並茂,描寫行為藝術,作者是溫普林,人家介紹説,他也是這裡的編導。我記起來,我在學校實習的時候,曾經採訪過這個人。普林、普慶是兩兄弟,住在北京城正北方的一個院落裏,開了一個文化傳播公司,養了很大的一匹狗,那狗的兇猛當時讓我很害怕。他們對於西藏頗有感情,因為正值青春年華時曾在那裏遊歷過,還帶著一桿槍,過著聽起來像是消逝已久的土匪的生活。當時我最能記住的是,普林説曾經不想讓自己的小孩上學,想讓他自由成長。我想,要是我的爸媽有這個觀點,我會是什麼樣子呢?
這些人各各個性斐然,我由衷地想,多像做紀錄片的啊。
後來又接觸到一位編導,華越。他用一種極其突然的方式讓我意識到自己頭腦簡單。當時我因事要找他,但還不認識他,所以進了他的辦公室後,看見一男兩女,拿不準是誰,就問:哪位是華越老師?只聽那位男士説,你找華越啊,他被抓走了啊,你不知道嗎?我很疑惑,兩個女孩子也十分歡喜地説:是真的,好久了,被勞教了。我再問:真的啊?三人都答:騙你做什麼!我半信半疑地回去報告了,邊走邊想,就像天才多怪癖一樣,這裡面恐怕怪人的比率也高一些。剛等我報告出這條"新聞",眾人便哄堂大笑。我義憤填膺地折回去,這回醒悟過來,那個躺在沙發上的頹廢分子肯定是華越無疑了。他們一看見我,樂得打滾。我臉紅脖子粗地想,怎麼要捉弄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呢,難道看出我的判斷力裏有點小Bug?後來我想,他大概根本就沒有想到能夠得逞,想不到我居然就範了。當時他正在為一部關於"三個代表"的片子日夜兼程,這個鬧劇無疑是一個苦中作樂的好機會嘛。
欄目的另一位製片人陳建軍在做一部曠日持久的片子《中華文明》,平時在梅地亞難得露面。劇組在北京的辦公地點是一個大倉庫,堆著許多遠古人物模型、陶瓷器具和膠片,像個神秘的工地。在那個"作坊"裏,陳建軍的辦公室頗為幽深,屋裏碼放著無數考古、地方誌、歷史書籍。他是周易學會的成員。
一部片子就是一個項目,人員的組合,散夥全依項目的需要而定,可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做片子的時候這裡可以熱鬧非凡,過了,也就恢復了平靜。而這平靜,又醞釀著不耐煩的閒散。這倒是很符合網絡時代的遊戲規則。
目前唯一固定的,是一項娛樂節目。陳曉卿有一個小孩子名喚樂樂,牙牙學語的年紀,看見"大"字就喊"大眾",看見"M"就喊"麥(當勞)",高興起來就像個小動物一樣叫喚,聲音嘹亮。除了這些表演,他的拿手項目還有,一聽到"跳舞"的指令,就咧著嘴左右磨牙;一聽到"放電"的指令,就低下頭,使勁翻眼睛。他總能夠給辦公室帶來吵吵嚷嚷的歡樂,讓人感到,思想與生活必定有某個可以貫通的渠道。
在這個時候,做紀錄片的散兵遊勇們暫時規避理想色彩,享受著普普通通的樂趣,紀錄人與生活也並不遙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