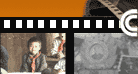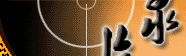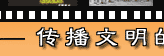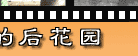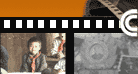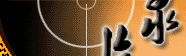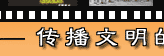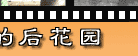讀到邵燕祥的一篇文章説,“我相信,性格即命運,也相信,政治即命運,更相信,性格如果碰上政治,那就是宿命了。”這樣表達過去的年代,有種隱隱約約的沉痛。但是文字克制的好處在於,它給人留下很多出口,去聯接各種相干或不相干的東西。盡可以把那些未知的溝壑,那些默默無聞的人或事以想象來舒展。歷史課本的面目之所以讓人不感興趣,因為它的判斷太多了,為人所用得太明顯,已經有結論的東西總讓我感覺到很不自由,比那些令人生厭的歷史演義更令人生疑。
歷史似乎總是和宿命聯絡在一起。我不願意認為它是先知先覺者們所説的規律,只能説它是一種無法控制的東西。我想,也許有人嘗試過將歷史做成個人命運的匯聚(記得有位外國的文學史家就以作家個人來做文學史的),去擺脫那些理論的空洞框架,讓歷史變得豐滿起來。從古到今,從生到死,人不是總在永恒的悲歡離合中品嘗命運的滋味麼,也許有些人似乎是自生自滅的,有些人卻可以改變別人的命運,有人生而為花,有人生而為葉,但這只不過是命運的形狀不同而已。但是不同時空裏,每個人的性格和選擇卻是活生生的,能夠引起人的興趣,因為這裡充滿了今人和故人的交流。
肖博士在做一部關於延安的片子,我跟著跑腿,也因此看了艾青等一些作家的傳記,更相信邵先生所言的準確。艾青選擇延安的時候似乎是猶疑不定的,儘管那是個叛逆成風的年代,他卻並不是富於革命激情的人,早先,他常常沉醉於鄉村的美景,後來又去巴黎尋求藝術的理想。同今天一樣,他似乎是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的。可是後來的故事超出了艾青的想象,他莫名其妙地坐了三年牢,在幾乎絕望的時候,開始寫詩,竟然因此而成名了。此後他只希望自己能夠有一桿自由的筆。但是戰爭來了。必須要選擇一個方向的時候,他又遇上了政治,他當時的妻子已經先他而作出了抉擇:到延安去。不久,他也這樣選擇了。這是他後半生的開始。
蕭軍是個暴烈率直的人,拄著拐杖,奇裝異服地走在統一的制服群裏,但是最終,這個有點遊俠氣味的人也落到了這片黃土地上。
而對於陳學昭來説,她作為最早的五四女作家和當時稀有的女博士,是頗有自由先鋒色彩的,她身上的那份理想主義在延安所經歷的瀝煉,並不止於以彈鋼琴的雙手來紡紗,以灰布制服和臉上健康的紅潤取代洋裝和美麗的傷感,更重要的是學會對於不熟悉生活的不曾有過的虔誠姿態。
丁玲的情形似乎有所不同,然而,掀開她當時對於革命的熱烈,從她的言辭裏,仍能看到她對於女人命運的無奈,負載了許多期望和失望的交織。
現在不能夠有這樣那樣的設想,去揣測當時的情形。他們都是一些敏感的人,嗜好自由的生活,但可惜也是軟弱的人,加上當時的情形似乎也缺乏更多的空間。命運中那麼多偶然的因素,可是結局卻何其相似,真如宿命一般。宿命就是説,你選擇了一次,也就選擇了很多次。我想,他們的選擇是值得紀念的,也許有不同的歷史形象,卻都是內心有過掙扎,這是他們在個人閱讀中的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