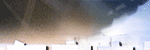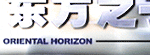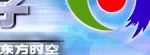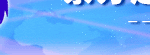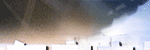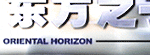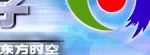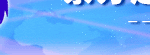|
| 03.11 14:36 |
 |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最近我們組裏的文學女青年們暗攢了一本組內刊物,取名為《子曰》。從此,我們每回正式説話前都要"子曰"幾句,好比文革年代"要鬥私批修這豬肉多少錢一斤"那樣。現在沒過仨禮拜,孔子的話就快引完了,只好搬出了莊子。
莊子曰:不知悅生,不如惡死。
編完一個不知所措的片子,等待一個不知所求的領導,進行一場不知所以的審查。這種情況下,不妨用莊子不知所云的昏話鼓勵自己度過難捱時光。
那天編完袁家騮,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和打掃衛生的清潔工一起奪門而入,而我像賊似的在《直通巴格達》的機房裏,已窩了一宿。仗不知什麼時候開打,我這節目可是第二天要播了。
夜裏三四點時,據説是人最脆弱的時候。總有大哭一場的衝動,因為天就要亮了,審片的人就要來了。那種無力回天的感覺真叫人絕望。
之所以絕望,是因為預感片子命運不濟。我用的幾段資料信號實在太差,這是我惟一擁有的、主人公還活著的資料。片子做著做著我又在陷入了情感主題,這是我惟一還有一些感覺的地方。可這種有人類社會以來就存在的主題,在新聞大戰日趨激烈新聞頻道即將開播的今天難道不應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嗎?--我聽到傳來誰的聲音。
我想好了,等製片人看完片子,如果他搖頭我就作啞,如果他罵人我就裝聾。如果他讓我大改,我就把莊子曰的後半句話拋出來以示明志。
誰知道十個小時以後這片子不僅不用大改還得了幾句表揚。我要知道我就能提早十小時悅生了。那個早晨在回家的路上我也不必給早起的鳥兒看一張苦瓜臉,完全可以趁"早晨空氣好我們起得早"一路哼唱"小鳥在前面帶路風兒吹向我們我們像春天一樣……"
其實在做這個片子之前,我曾憋著一口氣要弄出個什麼新花樣來,以此證明老區人民也有創新思維。但是接袁家騮這活兒時發現這很難辦。人沒了,生前影像也沒有,連追悼會的鏡頭都沒借著。他海外生活幾十年,國內師生朋友極少,據説連兒子對他都不了解,倒是天津有一妹妹和她關係不錯,但通篇讓妹妹談哥哥,這種視角好像不大對勁。又不是安吉莉娜�茱莉和她哥。
那天夜裏,我坐在策劃組門口(的電腦旁)直嘆氣,嘆如何向老區人民交差。無端地想起毛主席1949年某夜坐在延安窯洞門口遙望北京説的那句著名的話:進京趕考,考不及格是要回井岡山的。幾乎做好了萬一不成另外找地方混的打算。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就是井岡山來的人!
沒想到,心中一想起毛主席事情就好辦起來,那天半夜三更我竟然找到了江蘇太倉廣播電視局局長家的電話。因為剛聽説袁家騮第二天一早就要在太倉下葬,那是吳健雄的家鄉。那裏應該和我的家鄉一樣,現在正開滿了金黃金黃的油菜花。托地方檯給拍點鄉野的油菜花,也比在辦公室裏幹坐著嘆氣強。
沒想到袁家騮當天已經安葬了,他們那兒也根本沒有什麼油菜花。不過局長十分痛快地給了我太倉電視臺負責人的手機號碼,沒想到這負責人以前拍過袁家騮好幾次,沒想到她手中還有吳健雄活著的資料。
第二天到西單書店買了一本《袁世凱家族》、一本《吳健雄傳》,又站在書店角落裏蹭讀了一本《科學家夫婦傳記》。看到他們在伯克萊大學校園裏的結婚照,和初遇時兩人青春綻放的樣子,怦然心動,想起"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想起葉芝的《當你老了》,想起席慕容的《一顆開花的樹》。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候
我就愛這樣瞎聯想。在我最有創意的時候。
可是還有多少人會讓你一下子想起少年時代讀過的詩呢,當你老了。
靈感陣陣來襲,勢不可擋。接著又想到片子可以採用這樣一種倒退式的結構方式,從死亡開始,到出生結束。從生離死別白髮蒼蒼,到年富力強功成名就,再到青春年少意氣風發。在回溯中,死的冰冷越來越淡遠,生的美麗越來越清晰。最後回到生命的起點。
最後黑場,來一段字幕:
1913年,袁世凱做皇帝不成,死了。袁氏家族從此在恥辱中日益敗落。
這一年,他的孫子袁家騮三歲。
一個人也許無法選擇出身,但可以選擇如何生活。
瞧瞧,多深沉!愣不像無聊小報那樣拿袁世凱大炒特炒,只在片尾輕描淡寫一句,而且傳達出一種高級的生死觀,那就是,死亡是冰冷的,但如果一生事業有成美人作伴,且相信有人在天堂等你,死何足懼!
想到這些,我激動起來,在寒風中一口氣疾走了兩站地。連人生片斷之間用什麼畫面串聯都想好了。字幕,加上流水,做成倒流的效果。或者讓攝像在天津拍個老式座鐘,我在後頭做手腳,讓時針倒著走。營造回溯的意境,寓意恰似"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其實這根本算不上什麼創意,韓國導演李滄東的《薄荷糖》就這麼拍的,看碟人都知道。他選擇的回溯意像是倒退的火車。我模倣他,純粹是出於崇拜之心,如果成了,就算是向大師致敬吧。如果沒成,就算是給大師留點面子吧。
我還把這些想法藏住了沒對人説,一怕有人乘亂先用了,這年頭,第二個把姑娘比作鮮花的就是傻瓜。二怕把製片人的胃口調高了,歷史經驗證明,這很不利於片子通過及評級。
然而,可是,終於,一切的形式創新及主題開拓之密謀,在那個絕望的早晨宣告破産。我依然用傳統的方法講了一個依然傳統的故事。"千萬別大改"的願望依然成了那一刻心中的最強音。
然而,可是,終於,如果片子中稍稍還有一點讓我自己觸動的東西,可能是一個人的無可排遣的孤獨。這讓我想起了我遠在兩千公里之外的母親,七年前逝去的父親。以及若干年後的自己。
還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傷感與幸福。
編一個片子,想起幾句詩,想起一些人,想起與這片子完全不搭調的家鄉。這種濫情當然不會出現在片子裏。我得好好藏著它們。
十年前讀到過馬克�吐溫的一句話,一直記得。他嘲諷紐約的文人,説他們如同試管裏的蚯蚓,他們從彼此身上吸取養分,而不是從泥土中。
多年來,這句話如同一記鞭子,總讓人不能心安理得地變成一個自以為高級的小資。這對一個自小與人群疏離、習慣在書桌前眺望世界的人來説,是很難受的。尋找泥土,到泥土中尋找養分排遣孤獨,是每一條蚯蚓的宿命。
不過好在還有一些來自新鮮泥土的蚯蚓,甚至有俗世中的地龍盤龍和傳説中的臥虎藏龍什麼的。他們也是同類,卻能稍稍填補遠離泥土的空洞。雖然有些我從來不曾也永遠不會謀面。
●《東方之子》周文飛 2003、3、7淩晨
|
|

責編:復蘇 來源:CCTV.com
|
|
|
 |
|
 |
|
|
|
 |